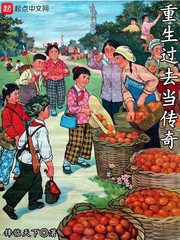穗竹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爱米文学网aimiw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贺徵朝进了车厢,垂眼望她一直没舒展的眉头,手背轻轻拭过,本不打算吵醒她,但温知禾却眯起眼,以浓厚的鼻音小声嘀咕:“回来了……”
稀松平常的一句话,入耳听进心里,隐约牵动着某处,莫名中带了些理所应当。他没去细究,也许是今夜的无风无月,让人不由松懈平和。
贺徵朝没挪开手,指腹撇开她额边的碎发,眸光凝瞩不转:“嗯,回来了。是等很久困了?”
其实他只让她等了二十分钟,也许是今天竞拍得太投入,又有痛经发作的缘故,温知禾一上车就没忍住睡着。
人一旦紧绷太久进入睡眠状态,难免会意识模糊,说话不太清晰,好比在上课时强撑的学生,笔记有在记,记的是鬼画符;老师的点名有听见,回的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话。
温知禾就是这样,她知晓自己得乖乖回话,梦里有多清醒,现实就有多颠三倒四。
她哼唧咕哝些含糊不清的话,饶是贺徵朝俯身去听,也听不出个所以然。
深究她的梦呓,本是毫无意义又浪费时间,罕见的是,他却是愿意这么做。攥着她外露的发热的手,贺徵朝垂眼,低缓的声线悄然凿开梦境的屏障:“再说一遍,我没听清。”
“听不清就听不清……又不是头回等……”温知禾闷声说,带了些嗔意。
贺徵朝不恼,带些若有似无的笑腔,像不信:“等过我几回?”
温知禾又开始嘀嘀咕咕,他凑得更近,挡了光且攫取新鲜空气,几乎要贴面触及鼻尖。
梦境深受现实外界的影响,温知禾以为自己在擤鼻涕,实则把头凑过去,埋到贺徵朝的领口里。她乖顺地找了个舒适的姿态窝靠着,眼底慢慢湿润,回得滞涩清晰:“好几回。”
她的头颅抵在下颌,面颊紧贴肩胸,忽视座椅间的分界线,完全倾靠于他怀里,轻悄悄、又沉闷地堵着胸膛,抑制他的每一次心跳。
贺徵朝低眉看她,只能瞥见乌黑的发,浓密颀长的睫毛。
温知禾没少和他演戏。每一回每一幕,演的是哪出戏,索要的是什么,他心里都有底。唯独这回,他却不觉清明。
他喉结滚动了下,耐心细问:“为什么等我?”
隔了许久许久,怀中人才回应:“……想你了。”
他还未有所反应,温知禾的头一滑,落在胸腔,两只臂膀隐隐有力地圈抱他,小心翼翼:“妈妈……”
纵使她说得再含糊不清,听二字的声调,贺徵朝也不难辨别。
她果真说的是呓语,根本不识在和谁谈话,俨然把他当成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