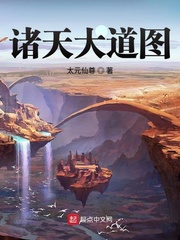加·泽文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爱米文学网aimiw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你的意思是你不喜欢他?”我问。
“不,我对他没意见,”她说,“但我越想越觉得,应该让你知道,取消一场婚礼并不比办一场婚礼更难。”
“什么?”
“我想说,这件事的确很吸引人,”她说,“事情一旦开了头,再停下来就很难。想想希特勒,瑞秋。”
这世上没有任何人能比希特勒更让妈妈不齿的人了。她极少提起他,但凡真的提起他,那一定事关重大。“我不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妈妈。”
“或许在某一时刻,那个人渣也曾经对‘最终解决方案’产生过怀疑。倒也不一定,因为他不是个善于自省的人,总之谁也无法确定。可是当犹太人被屠杀了一两百万的时候,在他病态的内心深处,或许也曾偷偷地想过:‘够了。这样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反而制造了更多问题!真不知我当初为什么会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可当时他的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于是就……”
“你真的要把迈克与希特勒相提并论吗?”
“不,在这个比喻里,你才是希特勒,你的婚礼就是‘最终解决方案’,而我则是有良心的德国人,不愿意袖手旁观。”
“妈妈!”
“别这么较真。我只是打个比方。大家讲故事都是为了讲道理。”
“你可不是!你不会这么做,起码不会拿希特勒讲道理!”
“你冷静一点,瑞秋。”
“你为什么要说这些?你是不是知道什么跟迈克有关的事?”毕竟这个女人曾经说过,她不知道什么是幸福。我实在想不出这是怎么回事。
“我什么也不知道。”她说。
“看你的样子就是知道。”
“我什么也不知道,”她说着从包里拿出一个装有柠檬硬糖的铁皮盒——母亲身上永远都带着糖,“你要一块吗?”
“不要。”
她耸耸肩,把盒子放回包里,“我什么也不知道,”她重复了一遍,“但我觉得,他并没有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你身上。”
我的手直发抖:“那他把心思放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她说,“但你是自由之身,我的女儿,你还有别的选择。你的确买了那双鞋,但你可以穿着它去听歌剧,而不是参加婚礼。这双鞋穿到剧院会非常出彩。我想说的就这么多,”她微微一笑,拍拍我的大腿,“那双鞋非常漂亮。”
我婚礼上穿的正是那双鞋,结果在走出教堂的时候扭伤了脚踝。整场婚宴上我都一瘸一拐,根本没法跳舞。
母亲的建议总是十分可靠。
4
我给艾伯丝的答录机留了一条啰里啰唆的语音留言:“艾伯丝,我是你以前的邻居,瑞秋·格罗斯曼——”那时候我还叫瑞秋·格罗斯曼,“茂林乡村会所的瑞秋·格罗斯曼,住在普林斯顿路,博卡拉顿,佛罗里达州,地球,哈哈!说正经的,我近来想起你,还有孩子们——”天啊,这可怎么说,“还有孩子们小时候的情景,所以我想约你吃个午饭,叙叙旧。”
过了一个星期,她也没给我回电话。她为什么要回电话呢?牛胸肉她吃了,三文鱼她也吃了,我们还是没能成为朋友。我决定往她的工作单位打电话。她的秘书让我等了一会儿,听筒里的彩铃是《三大男高音圣诞演唱会》专辑,我记得自己至少听完了两首不同版本的《圣母颂》,她的秘书才来回话:“艾伯丝在开会。”
“她真的在开会吗?”我问。
“当然了。”他说。
我开始盘算,是不是应该给她递张匿名字条,把婚外情的事情告诉她。可我怎样才能保证字条只有她一个人看见,而不会落在秘书或其他外人手里呢?
我正在琢磨要不要直接开车到她办公室去——她工作的地方在棕榈滩镇,车程四十五分钟——艾伯丝忽然回了电话。
“瑞秋,你好,”艾伯丝说,“接到你的电话我太惊讶了。你过得怎么样?迈克医生还好吗?阿丽莎呢?”
放在平时,这样的错误准会让我心生芥蒂(我们可是邻居!阿维娃举办成年礼时还邀请了他们家!),不过此时我心里却松了口气,她连阿维娃的名字都不知道,说明她对这场婚外情一无所知。“阿维娃很好,”我说,“她如今在众议员的竞选团队里实习。”
“我竟然不知道,”艾伯丝说,“真是太好了。”
“是啊。”我说。
我知道事不宜迟。
可我总不能只用一通电话就毁掉一个女人的婚姻啊。
“要不要一起吃午饭呢?”我说。
“哦,瑞秋,”她说,“我非常想去!但我实在太忙了,工作的事情很多,议员换届选举也很忙。”
“用不了多长时间,”我说,“哪怕只喝杯饮料也好。”
“我最早也要等到今年夏天才有时间。”艾伯丝说。
我必须得找个借口跟她见面,一个让她无法拒绝的借口。我想起阿维娃说竞选需要筹钱。那就谈钱,我心想。
“是这样的,我给你打电话不只是为了叙旧,而是想跟你讨论举办一次筹款活动,”我说,“不知你听说没有,我最近当上了博卡拉顿犹太学校的校长,我一直在找机会,把犹太民族的杰出人士介绍给我们的学生。所以我想,假如学校举办一次购票入场的夜间演讲会,由议员先生主讲,这样不是很好吗?让我们的学生了解议员先生,家长也可以参加,好好办一场活动,这对我们和议员先生都有好处。由博卡拉顿犹太学校举办的犹太裔领导人之夜,我们能不能谈一谈呢?”
她大笑起来。“只有事关竞选,这些‘饲养员’才肯放我出来,”她语气有些难为情,“下个星期四一起吃午饭怎么样?”她说。
为了这个重要的场合,我在洛曼百货买了一身盛蔷的西装。衣服是黑色的,带有金色的纽扣,镶了白边。衣服的折扣很大——在佛罗里达穿这种布料太厚重了——还算合身。
洛曼百货的试衣间是敞开的,也就是说,其他人也能看见你试穿衣服,并对你的衣服发表意见。
“你穿这件衣服非常漂亮,”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比现在的我要年轻)对我说,她只穿着内衣、内裤,颈上戴一条粗重的绿松石项链,“非常苗条。”
“这个风格不太适合我,”我说,“你的项链很漂亮。”
“这是我去新墨西哥州的陶斯镇看望儿子时买的。”她说。
“我听说那里很漂亮。”
“就是一片荒漠,”她说,“要是你喜欢沙漠的话,还不错。”
我挥了挥手臂,感觉自己好像穿了一身盔甲。
“这件西装简直是为你量身定做的。”那位上了年纪的女士说道。
我望着镜子中的自己。一个穿西装的女人,土里土气,神情严肃,像是监狱里的女狱管。她跟我一点也不像,这正是我所要的效果。
我赶到饭店时,艾伯丝已经到了,同来的还有一位负责为莱文议员筹款的主管,具体头衔我记不清了。他叫乔治,十分面善,可我却恨不得拿起叉子戳他。她居然带了外人来!我只好虚情假意地开始讨论那场子虚乌有的筹款活动。这顿苦不堪言的午饭吃了四十五分钟之后,艾伯丝说她有事,得先走,让乔治跟我继续讨论筹款事宜。“真是太好了,瑞秋,多亏了你,我才能从办公室出来透透气。”
“你这就要走了?”我说。
“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再聚。”她的语气再清楚不过,我们不会再见面的。
我望着她离开,等她走过门口的迎宾台时,我站起身,说:“乔治。”
“怎么了?”他说。
“不好意思。我得去一趟卫生间!”我意识到这样详细地说有些反常,但我不想让他猜到我真正的动机。
“好啊,你不用等我批准。”他轻快地说。
我按捺着步伐向卫生间走去,然而刚过迎宾台,脱离了乔治的视线,我立刻向停车场飞奔而去。谢天谢地,她走得不远。我像疯子似的一边跑一边大声叫她的名字:“艾伯丝!艾伯丝!”
滚烫的路面几乎融化成了沥青,我的鞋跟陷进了地面,我跌倒在地,擦破了膝盖。
“瑞秋,”她说,“天啊,你没事吧?”
我连忙站起身:“没事。只是……地面太黏了,”我说,“我真是笨手笨脚的。”
“你真的没事吗?我看好像流血了。”她说。
“是吗?”我笑了起来,好像我的血是个有趣的笑话。
她对我微笑:“我说,这次见面真开心。能跟你相聚我很高兴。我们应该……没错,你真的流血了。我好像有个创可贴。”她在手提包里翻找起来,那个亮面皮包呈五边形,边角包着黄铜,约摸有一个小行李箱那么大。总之,这个皮包可以当武器用。
“你随身还带着创可贴?”我没想到她这种人会随身携带创可贴。
“我有好几个儿子,”她说,“几乎算半个护士。”她继续在包里翻找。
“没事,”我说,“正好应该让伤口透透气。这样血凝结得更快。”
“不,”她说,“这种说法只是以讹传讹。受伤的前五天,应该让伤口保持潮湿,这样愈合得快,又不容易留下疤痕。找到了!”她递给我一个印着恐龙图案的创可贴,“你应该先把伤口清洗一下。”
“我会的。”我说。
“我好像还带了抗菌药膏。”她又开始在包里翻找。
“你这个包简直是魔术师的帽子。”我说。
“哈。”她说。
“好了!”我说,“你不必费心了。”
“好吧,”她说,“我们有空应该再聚。”
于是我说:“是的,的确应该再聚。”
于是她说:“你还有什么事吗?”
我知道,若现在不说,就再也没机会了,可我就是张不开口。这种事情实在没法说得委婉动听,我只好直接说:“你的丈夫跟我的女儿有婚外情,我很抱歉。”
“哦。”她说。短短一个字,那音调让我想起了心脏监测仪上的那条横线:高亢而决绝,透出死亡的意味。她抚平自己身上那套西装——深蓝色,跟我身上这件几乎一模一样,又整理了一下稻草人似的直发——在这片地狱一样的停车场站得越久,她的头发似乎就越蓬乱:“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呢?”
“因为……”因为我母亲让我来找你?我究竟为什么没有去找他呢?“因为我觉得这是女人之间的事。”我说。
“因为你觉得,假如我不施加压力,他就不会分手。”
“对。”
“因为你不想让你女儿知道你出卖了她,”艾伯丝继续说,“因为你想让她爱戴你,把你当成她最好的朋友。”
“对。”
“因为她是个荡妇——”
“拜托,”我说,“她只是个犯了错的孩子。”
“因为她是个荡妇,”她说,“而你是个懦夫。”
“对。”
“因为你想制止这件事,你觉得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对。”
“因为你看看我丈夫,再看看我,你觉得我早就经历过这种事。是不是?”
“我真的很抱歉。”
“抱歉有什么用。我会处理的,”艾伯丝说,“我会告诉乔治压根就没有什么筹款活动。狗屁犹太裔领导人之夜!下次你再想把别人的婚姻搞砸,在他妈的电话里说就行了。”
我满心愧疚,但却轻松了不少。我把自己的负担转移到了别人身上。我回到饭店跟乔治喝了一杯伏特加汤力水。我问他,在莱文夫妇手下工作是什么感觉。
“他们人非常好,”他说,“才貌双全,真是再好不过了。大家都觉得他们是天生一对。相信你也看得出来,对吧?”
5
在遇见那个浑蛋路易斯之后,我决定把网上交友这件事先放一放,安心地给罗兹和卖玻璃的托尼当电灯泡。这位玻璃商人说他很乐意与两位女士相伴,而且说实话,他才是真正的电灯泡,因为我和罗兹的友谊比他们的恋情开始得更早。
罗兹和托尼打算在克拉维斯演艺中心订购百老汇剧目套票,罗兹想让我也一起订。三张联排座位?我说,那我可真成了你们俩的电灯泡了。她说,那又怎样?托尼说他愿意坐在中间。
于是我们每个月都会一起看场剧,托尼和罗兹来接我,先找个地方吃晚饭,然后再去剧院。看完第一场剧——《歌舞线上》以后,托尼就开始叫我“腿女士”。他说我长了两条舞蹈演员的腿。我说我长的是跳普拉提的腿。罗兹则说自己长了两条火鸡腿,脖子也像火鸡一样松松垮垮,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就是这样。或许算不得深情厚谊,但也可谓其乐融融,正适合打发时间。
第三场剧是《卡美洛》,罗兹有点咳嗽,不能去看。罗兹说她不想整场剧都咳个不停。我说这里可是南佛罗里达,音乐剧场里的咳嗽声比音符还多。话虽如此,罗兹还是说,她可不想加入南佛罗里达的老年咳嗽合唱团。
于是托尼单独跟我去看剧,吃晚饭时我们谈起了罗兹。他说自己能遇到她实在是太幸运了,她填补了他生命中的空缺。我则说,这世上找不到比罗兹·霍洛维茨更好的人了。他又说,他很高兴能与罗兹的朋友也成为朋友。
音乐剧唱到一半,当桂妮薇儿<a id="z7" href="#z7"><sup>【7】</sup></a>唱《爱欲洋溢的五月》时,他的胳膊肘越过了座位之间的扶手。我把它顶了回去。到了第二幕,桂妮薇儿演唱《我曾在沉默中爱恋你》时,那只胳膊肘又回来了。这次我把它一下推回了他的座位。他对我笑笑:“抱歉,”他耳语道,“我块头太大,剧院都装不下了。”
往停车位走时,他说:“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长得非常像伊冯娜·德·卡洛<a id="z8" href="#z8"><sup>【8】</sup></a>?”
“你是说吸血鬼夫人?”我说,“她还在世吗?”
他说在那部剧之前,她还演过许多其他角色:“《十诫》里面扮演蛾摩拉<a id="z9" href="#z9"><sup>【9】</sup></a>的不正是她吗?”
“蛾摩拉不是个角色,”我说,“是座城市。”
“我很确定她演的就是蛾摩拉,”他说,“那部电影我看一千遍了。”
“那是个城市,”我说,“一座充满暴力、令人作呕的城市,里面的居民对人满怀恶意,大行淫荡之事。”
“什么样的淫荡事?”他说。
我才不会上他的当。“好吧,”我说,“随便。”
“你怎么就不能对我和蔼一些呢,瑞秋?”他说,“我喜欢你对我和颜悦色的样子。”
送我回家时,这位玻璃商人费了好一番口舌,坚持要把我送到门口。“不必了,”我说,“我知道家门口的路该怎么走。”
“对你,就应该提供全套服务。”他说。
“我没事。”我说。
“我答应过罗兹要送你回家。”他说。
我们往家门口走,到了以后我说:“晚安,托尼。替我向罗兹问好。”
他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拉到他身边。他通红肥厚的嘴唇紧紧吸住我的嘴唇不放:“你不想邀请我进屋吗?”
“不,”我扭开嘴唇,挣脱手腕,说,“你会错意了。罗兹是我最好的朋友。”
“别装了,”他说,“你跟我眉来眼去已经好几个月了。别抵赖。”
“我绝对没有!”
“女人对我暗送秋波,我觉得我还是看得出来的。对于这种事情我很少出错。”
“这次你真的大错特错了,托尼。”我从包里翻出了钥匙,但手却抖个不停——因为愤怒,而不是恐惧——一直打不开门。
“那你总说要教我普拉提是怎么回事?”他说。
“那是我的工作,”我说,“而且我确实认为,只要加强腹部锻炼就能帮你缓解坐骨神经痛。”
“今晚你就可以帮我锻炼腹部。”他说。
“你该走了。”我说。
“好了,放轻松。”托尼说着,开始用他那凹凸不平的厚手掌摩挲我的肩膀,感觉很不错,但我并不想让他把手放在那儿,“别这么不解风情。对这种事,我跟罗兹早有共识。”
“不可能。她不是那种人。”
“你并不了解罗兹。”玻璃商人说。
“对于罗兹,我一清二楚。即便你们‘有约在先’——且不管我信不信——我也不要你!”
我把钥匙插进锁孔,他想跟在我身后闯进房间。我一把推开他,把他的脚从门槛上踢下去,关上门,插上了插销。
我听见他直喘粗气,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希望你不要太幼稚,瑞秋。”他的意思是,他不想让我把这件事告诉罗兹,而且他希望百老汇戏剧之夜能够照常进行。
玻璃商人终于走了,我想给罗兹打电话,把这件事告诉她,但我没有这样做。毕竟没有真的发生什么事。要想生活没烦恼,该管住嘴的时候就得管住嘴。
六十四岁的我仿佛再次回到了高中。
尽管托尼的不忠让人备感压抑,并且让我为朋友感到悲哀,但是我想讲给罗兹听的并不是他的不忠,而是想把这个故事告诉她。
我盯着电话,竭力遏制自己给罗兹打电话的冲动,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
“罗兹?”我说。
原来是那个浑蛋路易斯。“我反思了很长时间,”他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我说错话了,对不起。我不该那样评价你的照片。”
“什么评价?”我说。
“我不想再重复一次了。”他说。
“恐怕你必须得重复一次。”我说。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说,你本人比照片漂亮多了。我那样说真是太蠢了,”他说,“你说,你听到这样的话该怎么回应?你是不是觉得我在诋毁你的判断力?还是你觉得我是在说你的照片难看?你的照片一点儿也不难看,瑞秋,你的照片非常迷人。”
我告诉他,并不是因为这个。
“那是怎么回事?”他很想知道,“一定有问题,我知道一定有问题。”
我对他说:“可能我只是不喜欢你。”
“不可能。”他说。
“晚安,路易斯。”我说。
“等一等,”他说,“不论我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你能不能试着原谅我?”
“晚安,路易斯。”我说。
我还以为文学教授都是聪明人呢。
依我看,他说出那番有关阿维娃的话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早点搞清一个人的真实面目是件好事。
6
我一直在等阿维娃的电话,等她向我哭诉议员的妻子发现了这段地下情,议员跟她分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