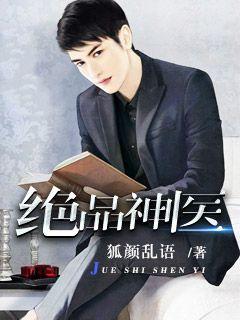塞巴斯蒂安·巴里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爱米文学网aimiw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春天终于降临在马萨诸塞州,带着她那明丽火焰。上帝的呼吸将暖意吹进万物,寒冬就此被驱逐。大伙儿驻扎在波士顿老城外围,一个名叫长岛的地方。尽管也会绵绵不断地下雨,雨幕稠密得像布,也没完没了地敲打着营帐,但我们有了新事业,每个人的心中也真的滋生出一种使命感。这是我们准备投入战争时的整体面貌。
绝大部分装备火枪,斯宾塞卡宾枪只有寥寥几把,正因为如此,当初斯塔林·卡尔顿看到“第一个抓住马”居然有斯宾塞卡宾枪时才会无名之火顿起。还有手枪,其中几把是牌子比较响亮的转轮手枪——勒马特短枪与柯尔特手枪。另外还有一些长刀、马刀和刺刀,我们手头可以用来对抗叛军的武器差不多就这些了。值得一提的是一批新型子弹,是我们射杀印第安人时没见过的。不同于老款的圆形子弹,这批新货的形状像是教堂入口拱门的形状,头尖尖的。少校如今穿上了上校的制服,从波士顿的一片烟雾臭气中征召到了大把大把的爱尔兰人。有装卸工,有挖土的和铲煤的,有赶大车运货的,还有无赖小混混,有整天夸夸其谈的莽夫,也有胆小如鼠的毛头小子。管他是什么货色,都行,因为我们必须扩张成一支庞大的军队。约翰和我是下士,被分派的职务是班长,因为我们是真的当过兵的,有从军经验。少校把斯塔林·卡尔顿也弄来了,他眼下的军衔是中士。一起来的还有利戈·马根,他现在年龄更大了,差不多有五十几岁了,所以也被提升当了中士,负责扛军旗。所有其他的人,都只是普通列兵,志愿兵,联邦的忠实支持者,还有进来投机撞大运的。这里有一千张面孔,而我们最熟悉的,应该说是在D连队。我们签了三年的服役期,每个人都认为,战争所需的时间不会超过三年,要是再长,我们可就不信上帝,不当基督徒了。列兵们大部分只签了九十天的服役期,他们只打算完成义务,完事之后就回家。我们在那坑坑洼洼的练兵场上出操训练,往复来回,中士们教菜鸟新兵怎么给火枪上弹药,但老天做证,那些傻子学得可真不快。装十枚子弹,假如只掉出了一枚,那已经算是非常优秀的了。谢里丹、狄南、奥雷利、布拉迪、麦克布莱恩、莱萨特,一连串的都是爱尔兰名字,跟他妈的密西西比河一样长。有几个小伙子曾在马萨诸塞的民团自卫队混过,所以不至于也那么笨手笨脚。“可是,万能的上帝,这算什么啊。也许,林肯先生还是应该担心一下的吧。”约翰整天这样念叨。他在一旁观摩新版训练,一脸茫然,这些人连最基础的操练都能搞砸。斯塔林是前一天过来的,一来就嘘寒问暖,嚷嚷着战友情深什么的。他拥抱了约翰,我可以发誓,因为久别重逢的喜悦,他几乎都要亲吻约翰了。利戈·马根握着我们的手用力摇了摇,说重新遇见我们,相当于是在新战争里邂逅了两个新朋友。“初次见面,请多关照,两位过得怎么样啊?”他煞有介事地问候我和约翰。我们说过得挺不赖。“那个印第安小妞呢?”斯塔林问。“哦,她也非常好。”我说。
少校那时在参加一场婚礼,忙得跟东奔西颠拯救人世的耶稣似的,但他还是抽身过来了,以他特有的方式冲我们微笑,说尼尔太太向当年军营的旧相识们问好。这让我们笑了起来。斯塔林·卡尔顿觉得这是个实打实的玩笑,笑得前仰后合,少校倒也没觉得受了冒犯。他转头看看大家,左顾右盼,一边使眼色,一边从他那老旧的军便帽上甩去汗水。“我知道,你们都会全力以赴的。”少校说道。“是的,长官。”利戈回应道,“去他妈的,我想我们会万死不辞的。”斯塔林说。“我知道你们会的。”少校说。他那身上校制服可真不赖。
“现在,小兄弟们,你们要服从上级的命令。”少校继续说道。他指的是威尔逊上尉,一个寡言少语的红头发爱尔兰人,还有萧内希中尉和布朗中尉(听上去都像十足的都柏林人,值得尊重),还有马根中士,以及两个下士班长,当然也包括我和约翰。然后就是克雷郡的人,西部沿海各地因饥荒逃出来的人,一个杂烩组合。这些家伙的脸色,就像泥沼中埋了多年的炭化橡木。更年轻一些的新兵,时而面带微笑,时而皱皱眉头,他们知道,原来的世界已经崩塌,现在最好祈求命运再给个机会,让他们有机会为一个新世界而战。就在我们开拔往华盛顿行军的那一天,威尔逊上尉站在存放马鞍的木箱上,发表了一通漂亮的演讲;我至今依旧能看到所有那些面孔,都盯着讲话的上尉看,每每想起那番情景,就会忍不住哭泣。“我们只要求你们能把联邦放在心中,跟随那颗星,让它引领你们。国家需要你们的付出,所需要的甚至超出任何人的承受极限。我们需要你们的勇气,你们的力量,你们的忠诚。你们可能会牺牲,会被迫面对死亡,但你们必须时刻保持勇气……”上尉这样滔滔不绝地演讲着。“或许这是他从什么文选手册里找来的辞藻吧,就像罗马人的演说那样。”斯塔林说,他看起来一脸茫然,像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姑娘。但就那么莫名其妙的,这演讲触痛了我们,让我们有了一种理解和感悟。当兵打仗,主要是为了领军饷,那次应该能拿到十三美元。不过,以前可不是那样的。血气方刚的时候,我们几乎能把敌人的头直接咬下来,嚼一嚼,把头发给吐出去。上尉来自威克洛郡,模样挺和善,一口美式英语如乐曲般动听。
我们行军前往华盛顿,四个兵团汇成一条闹嚷嚷的蓝色河流。抵达目的地之后,我们又被召集起来,接受高贵的大人物的检阅。那些人在远处,看上去只不过是些小黑点。他们的发言我们连一个字也听不到。“十有八九还是那老一套,同样的胡说八道。”斯塔林说,但任何一个傻瓜都能看出,他多多少少还是有几分自豪的。这阵仗可真够大的,全部的士兵都整齐排列,野战炮则闪亮着,带着近乎狂欢的气势和火星四溅般的荣耀感。更不必提那些士兵了,他们都穿戴得整整齐齐,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能多整洁就多整洁。两万人,那可不是什么稀稀落落的一个小群体。绝对不是。
丹·菲兹杰拉德是个挺不错的小伙子,因为会打牌,就跟我们凑在了一块儿。于是,这就很像从前在拉勒米堡的时光了,除了我们眼下是扎寨露营在稍稍有些位移的群星下。另外,这座城市中随处都是穿蓝色正装的绅士们。有家庭妇女过来,在洗衣处给我们槌捣翻洗制服,有很棒的小家伙唱歌娱乐,甚至连我们的鼓手麦卡锡,一个才十一岁的黑人小孩,也有一套把戏,算个人物。虽然名字听上去像爱尔兰人,但麦卡锡其实来自密苏里。密苏里人不知道该站在叛乱者一边还是联邦一边,于是,在他们还犹豫不定时,麦卡锡他自己就跑出来了。紧邻的一排帐篷中,住的都是个子高大的家伙,他们是负责操控迫击炮的炮手。就像你从未见过什么人有如此粗壮的大长胳膊,我们从未见过如此粗壮的炮筒,看起来就好像这些大炮一整年什么都不吃,就尽吃黑糖蜜了。人们说,到了里士满的城墙脚下,大炮就派上用场了,但斯塔林却说,那里根本没有城墙。因此,那传言是什么意思,我们就不知道了。
我们的连队基本上都是从克雷郡来的人,而菲兹杰拉德来自邦多拉哈,他说那是梅奥郡的一个地方,又脏又穷。我遇到的爱尔兰人,当中没多少愿意讲这些倒霉的黑暗往事,但菲兹杰拉德提到这些时,倒显得足够轻松。他有一支六孔小笛,其他类型的诉说,就用这锡口笛来抒发。他说,他的家人都在大饥荒中送了命,十岁的他翻山越岭走到了肯梅尔,然后辗转到了加拿大的魁北克。仿佛是奇迹,他跟我一样,一路也没发烧得坏病。我问他,在船舱中有没有看到哪个人吃其他人的尸体,他说他没看到那个,但看到的是更糟的。到了魁北克,当人们打开舱口门,把封舱的长钉子拔出来,四周时间以来的第一次,光线照进了船舱。整个航程中,他们唯一有的东西就只是水。在那崭新的光线中,他突然看到尸体漂浮在船底积水里,到处都是。奄奄一息的、熬到最后的人,都成了一副骨架子。或许正因为回忆凄惨,所以才没人愿意提起这经历,它本就不应成为话题。我们摇摇头回避了这个话题,继续发牌打牌。有那么一会儿,谁都不说话。面对尸体,我们也变得毫无价值,那种见解或领悟,就像火一样烧过我的大脑,还持续了一小段时间。曾经的我们只是废物,而现在,我们腰上缠上武器,我们要拼命,要获胜。
军营中不时也有激烈残酷的打斗发生,但那不是跟“黄裤腿”<sup><a id="noteBack_1" href="#note_1">[1]</a></sup>们作战。美洲本地出生的士兵,有些人挺害怕爱尔兰人的,因为后者心情不好的时候会主动滋事,抬脚猛踩你的头,直到他们自个儿觉得解气了。似乎每个爱尔兰人的肚子里都窝着大团的怒气,动不动就爆发,天晓得是个什么毛病。身为班长,我必须树立威信,是不是必须得发飙吓唬一下他们,否则他们不会安安静静地守着规矩。这可不容易。如果他们一直乱来,我就得把他们扔进禁闭室。他们当然是不情愿的,满怀怨恨的样子,就像猎狗嘴里叼着鸟儿一般。所以,我行事必须更加公正,像所罗门王一样公正。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爱尔兰人也可能是天底下最温和友善的。比如,假设你真饿得不行了,丹·菲兹杰拉德甚至愿意让你啃他的胳膊,只要能救你一命;再比如,威尔逊上尉是去年才从老家跑出来的,他说那地方的情况依旧在恶化,顺着大路就能直达地狱。但他自己可是个一流的人物,在编为国民军的威克洛民团担任少校团长,虽说手底下的人看起来都有些傲慢自大,但威尔逊本人却并不专横,不用蛮力打压手下,团里的人对他也挺满意的。他不管命令什么,手下都会立即执行。斯塔林说,爱尔兰士兵的麻烦在于,被吩咐去做什么事情时,得愣着想一想,也会在心里反反复复地掂量。他们瞪眼瞧着长官,
想看看那命令是让长官高兴还是不高兴。这对士兵而言可不是什么优点。每个爱尔兰人,都认为自己有理,是与正义同行的,为了证实这个,他甚至可以去单挑全世界。斯塔林说,爱尔兰人就他妈的是狼吞虎咽的狗。然后他大力拍打我的手,一边哈哈笑了。斯塔林,现在肥得跟头大灰熊一样的斯塔林,已经是中士军衔了,所以我不能猛击他几拳,尽管我很想。
丹·菲兹杰拉德与少年鼓手麦卡锡之间迅速萌生出了友谊。丹很热心地教麦卡锡练习一些爱尔兰曲调,两人用风干的骡子皮,还有拼接的木桶板条,做成了一面爱尔兰样式的鼓,再切削木条弄出一根小鼓槌。他俩踩着那些舞曲的鼓点瞎跑,边跑边敲鼓,军营中松散的落寞时光,也因此多了一些乐趣。但现在,那样闲散的时候已经不多了。我们慢慢地向前推进,进入弗吉尼亚州北部。我们原本还指望着,能听到说供大车开行的路已经铺好,但实际上根本就指望不上那个了。我们只能步行。
利戈·马根的小分队扛着大旗,那场面还真是值得一看的。挺漂亮的彩旗,据说是什么地方的修女尼姑们缝制的。我得让手下的人保持良好的纵队队形,约翰也有他的一帮人要维持秩序。应该承认说,斯塔林对他的军中业务还算懂行的,他所领导的连队,我们觉得也不差。事实上,所有人都处于狂热、亢奋的状态,渴望上层能尽快安排行动,然后就冲向叛军,杀敌报国。斯塔林显得庄重又有权威,尽管没有骑马,倒也有点儿岿然傲立、中流砥柱的意思。他雄赳赳地前行,一副势不可当的姿态。我们并不怀念以前老军士长行军时那要命的哼唱,不过麦卡锡倒是在他的鼓上敲出了进行曲——左、右,左、右。永恒的士兵生活,一切都仿佛是恒定不变的。我们不得不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点,唯一的移动方式就是急行军,那古老的一套。我们偶尔也会幻想着悠闲的旅途,慢悠悠地晃荡,弟兄们剥掉衣服,趴在溪流边喝水,经过农场时便精神一振,兴致陡增,期盼着有哪个贤淑好女人,烤好了糕饼等着我们。事实上,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不知不觉中,我们进入了两面派的领地,北弗吉尼亚,我们不知道忠于联邦的民众群体身在何处。不得不说的是,弗吉尼亚的自然风光引人入胜,道路西侧有高山屹立,古老的森林对我们不屑一顾,丝毫不把行人放在眼里。有人说,那里的农场都老旧不堪,失去肥力,几乎已颗粒不收,我倒觉得它看上去丰饶肥沃。四个兵团足以汇成一条喧腾嘈杂的河流,但鸟儿的鸣唱依旧穿透了鼎沸的人声,当地的狗儿们也来到它们领地的边缘,伸长脖子,抬着头对我们狂吠。行军背包,火枪,还有那面料粗糙的制服,我们都得自己扛着,不能嫌重,否则意志就会被压垮,时刻提醒自己“我是强壮的”才是对抗旅途疲惫的妙招。没人愿意仅仅因为搞不定南下到弗贞妮子——丹·菲兹杰拉德就这样称呼弗吉尼亚——的小小远足,就出局离队。无论如何,我们不是要去给那些叛匪上上课嘛,指出他们站错了队,走错了路,而是要让他们看看,我们数量庞大的武器究竟能干什么。驱使我们进军的命令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当兵的就是这样的命运。“反正就是指令我们去干掉那些叛匪。”丹·菲兹杰拉德说。有时候,我们一边走一边集体唱歌,弗吉尼亚的鸟儿在那听着,可我们才不会教给它们那种纸上印出来的歌曲版本,那种在努恩先生的剧场里会找到的版本。我们唱的是新版本,我们所记得的每个脏字,无数的咒骂,每个肮脏下流、无耻粗鄙、窑子里才说的粗俗词句,都被安插连缀到了歌词里。
行军开始之前,我寄了一封信给麦克斯温尼先生,说但愿薇诺娜安然无恙。我希望他收到信了。刚加入军队的头两个月,我们拿不到工资,以至于当大家伙儿终于领到薪水以后,欢欣鼓舞之情溢于言表,总算是可以给家里寄钱了,所有人都喜笑颜开,我和约翰也不例外。信奉天主教的随军乔瓦尼神父带着我们的薪水去往邮政驿站,将我俩合在一起的那笔钱汇寄到大激流城。士兵的汇款有专门的军用封套,而神父从不提什么刁钻狡诈的问题,不会问你妻子怎么样怎么样。约翰有女儿,这是个让人很容易随性发挥的话头,但这是一位友善随和、易于相处的人,全军上下的所有官兵,无论信什么宗教门派都喜欢他,毕竟,一副好心肠能跨越重重藩篱阻隔。乔瓦尼神父是个小个子,打仗是没多大用场,但当一个人对只有上帝才能知晓的未来感到迷惘时,当意志的螺丝钉开始松脱时,乔瓦尼神父就会开始履行自己的天职。行军几天后的牧歌夜晚,我一边轮值放哨,一边忙着宽慰邓尼希下士。我眼里心里都很清楚,这家伙正浑身发抖。当我们闲聊时,即使是在月光下,我也能看出他状态极不好。所以说,并不是每个人都盼望着能投入战斗、奋勇杀敌。乔瓦尼神父悄悄地摸过来,到了他身边,扶着他,开始给他打气鼓劲。无论如何,最好还是等到早上再看看情况吧。“班长,”他对我说,“你安排其他人来值班吧。”“我懂了,神父,听你的。”我说。
当我们抵达部队必须部署驻扎的场地时,狰狞可怕的危险气息减弱了。有消息来报,有人瞥见穿灰制服的叛军小子们进入了大片的条状林区,而树林看上去仿佛是在那野地上奔泻直下。三块巨大的长草地沿坡度抬升,高处是一块光秃秃的、草木凋萎的岬地。草地上的草长得很高,甚至达到三英尺,母牛看到的话,估计会迫不及待地冲过去饱餐一顿,我们的炮手以专业的手法算好射程才定下了炮位。到了下午,我们这一分支队伍已部署就位,情况挺好。士兵们心中有什么东西正确立成形,假如你能看到那东西的实体,它或许长有一对奇异的翅膀。那东西在他们胸中扑腾激荡,翅膀拍击的美妙声音哗哗作响。我们的火枪已经子弹上膛,我们五十人排成一行,单膝跪地,另外五十人站在身后一排,再往后是一排负责充填弹药的。一些神色焦灼却一声不吭的弟兄,时刻准备着冲上前来,填补空当。野战炮开始向树林中发射炮弹,转瞬间,我们便都惊奇地瞪眼观望那爆炸的场面。火光和黑烟在树尖上冒出来,然后你也许会想象森林的那一片苍翠会前后摇摆,试图把那被炸毁的地方覆盖起来。这些都是在四分之一英里之外,然后我们看到,穿灰衣的士兵出现在树木那缠杂交错的边缘处。上尉举着望远镜在观察,他说了点什么,但我听不见。话被大伙儿重述着,接力向后传递。听起来,他说的似乎是“那边有大约三千人”。那听上去像是个很大的数字了,但要知道,我们比那还多一千。高处草地上是那些“黄裤腿”的团组,我们的大炮现在要尝试把他们打倒在原地。我们真的做到了,炮还打得挺准,叛匪们不断向下转移,朝着我们发起反击,那阵势是我们从未预料到的,至少我没料到。当他们进入射程范围内,长官们让我们稳住,等了片刻才喊出开火的命令,我们听令开枪,疯狂的叛贼泥石流般大批大批地冲下来,英勇无畏的模样填充了死亡留出的空白。他们持续不断地冲锋,我们每一排的人,都忙着装子弹和开火,片刻不停。叛贼们有的也开枪还击了,有的暂时停下了脚步,站着举枪准备瞄准,还有的人一边往下冲,一边仓促开枪。
这场面根本不是之前所谓的“慢行军”啊,一大群活物潜伏在那里,突然就疯狂地飞奔而来。我们没想到这么多人会被射杀,也没办法阻止他们,前后左右的弟兄们陆续倒了下去,要么是脸上中弹,要么就是胳膊被击中,这些凶暴的“米尼式”小子弹能撕开柔软的肉身。上尉厉声嘶吼,命令我们装上刺刀,起身冲锋。我负责指挥的那一小撮人马,其中一个傻瓜仍带着迷糊的信念,单膝跪在那里,我迅速地踢了他一脚,让他起立,冲锋就此开始。我们铆足劲儿往前奔袭,但簇集的野草很稠密,兄弟们很难畅快地奔跑,一个个都跌跌绊绊、东倒西歪的,嘴里还不住地骂骂咧咧,就跟醉汉似的。但不管怎样,凭借猛烈爆发的一股蛮力,我们设法站稳了没倒下,并且急切地渴望与敌人短兵相接、贴身近战。意志战胜了身体所面临的困境,野草也不能阻碍我们的步伐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句“杀啊”,我们喉咙里就紧跟着发出了一串连自己都未曾听到过的声音,随之升起的是剧烈的饥渴,让人只想行动,却不明白究竟要干什么,除了伸出刺刀,捅进前面那奔流的一片灰色。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受涌动在胸中,我无法描述,因为那不属于惯常的言语话题范围。这次的冲锋与和印第安人激战不同,印第安人并不被我们视作同类,而此时此刻,我们就像是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厮杀。那些南方邦联的家伙,有爱尔兰人,英国人,还有其他各类人都在继续向前慢跑奔袭,慢跑奔袭,直到停止。叛军突然向右侧转,穿过那草地,他们已经看到我们的人马形成的巨大包围圈,正从后方席卷而来,仿佛一架准备完毕的死亡引擎。我们听到了长官们在一片混乱嘈杂中喊出的命令,要求停止冲锋,单膝跪倒,装弹药,开火。我们照做了。野战炮再次喷射出炮弹,邦联的那些士兵,像一大群野马那样止步了,接着往回跑了差不多十米,然后转头,把那十米又还回去了。他们迫切地想进入远处的森林,得到树木的庇护。野战炮在后方轰响,它们在后方喷出炮弹。有些炮弹打过来时已经很低,以至于也要从我们之间寻得一条通道。有一颗炮弹强行从大活人当中挤过,犁开一条可恶的血肉沟槽,我们行列中的不少弟兄因此倒下了。一种狂乱的疲惫倦怠侵蚀了我们,深入骨髓。我们机械、呆滞地装弹药开火,一片噪声中,几十枚炮弹打进了敌方人群,把他们炸成了碎片,炸成了肉丁,突然有一种悲惨和灾难的末日感觉。然后,一大丛花朵出现了,就如春日百花突然竞相盛开,草地变成了一张奇异的地毯,火焰的地毯。野草着火了,恣肆燃烧着,越烧越来劲,火焰彼此助长声威。草叶大簇大簇地燃烧,奔逃的士兵,他们的双腿受到洗礼,但那不是柔软青草的抚摸,而是暗黑的火焰,咆哮的蛮力。受伤的人倒在了那焚烧炉中,因为恐怖和面临死亡煎熬而鬼哭狼嚎。那样的剧痛,任何动物都没法忍受,肯定也会发出疯狂的尖叫,撕扯翻滚,暴跳挣扎。敌军队伍的主体还是寻得了树林的庇护,那些死伤的,现在被遗弃在身后焦黑的土地上。是什么促使上尉下令,让我们停止了射击,又是什么通过接力传达的命令,让大炮也停了下来?我们眼下就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风助火势,将烈焰吹向草地上坡,也把很多人,无论是在号叫的还是安静的,留在了身后,留在大火的遗迹上。火焰未曾烧到的其他地方,那里是呻吟低哼着的人们,垮掉的人们。我们收到了撤退的命令,蓝色的士兵潮后撤了大概两百码。一些弟兄和医疗兵从后方赶来,去执行无须带枪的特别任务,神父也来了。叛军树林那边也派出了医疗人员。双方都没说一个字,暂时停战的协定就这么在沉默中达成了。双方的火枪都扔下了,特遣分队的成员们现在也发起了冲击,但不是要开枪杀敌,而是忙着去踩灭残留的火苗,去救护被炸得缺胳膊少腿的、浑身烧伤的、濒临死亡的伤员。人们在那片烧焦的草地上争相忙碌奔走,仿佛一场诡谲的舞蹈。
注释
<a id="note_1" href="#noteBack_1">[1]</a>“黄裤腿”指南方邦联正规军士兵,因制服裤子为棕黄色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