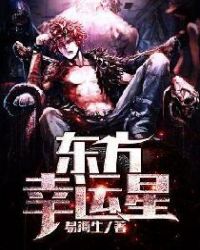西蒙娜·德·波伏娃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爱米文学网aimiw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我笑了一笑:
我又贴着墙头溜过去,闪进门廊躲藏,在枪林弹雨中穿越,到达《国民报》的大楼时满身是汗,衬衣上血渍斑斑。我想到了阿尔芒的微笑,当我跟他说加尼埃牢固地占领着市郊时,他眼里必然会闪烁喜悦的光芒。
“不完全一样。”
“我会告诉他们的。”
“可是您的命运应该与人类的命运密切结合,既然您将和人类长期存在下去。”
“告诉他们,我们会坚持到天亮的。”
“我可能还更长久,”我说。
我在他身边坐了一会儿;他用牙齿撕碎了几块白布,全神贯注地把碎布往弹壳内填;他的这双手不灵巧;他并不想制造弹药,他愿意演讲,这个我知道。但是,直到我站起身,我们没有交换过一句话。
我耸耸肩膀。
“我没有算过。”
“您说得对,”我说,“牢房的生活叫我累了。这会过去的。”
“死了许多人吧?”
“这肯定会过去的,”他说,“您将看到我们会做出多么出色的工作。”
“军队进攻了两次。都给我们挡回去了。”
共和派内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部分人依然维护资产阶级的特权;他们主张自由,他们只是为自己的私利而主张自由;他们只希望政治改革,反对订立任何社会条例规章,认为这只是一种新的约束。阿尔芒和他的朋友恰恰相反,主张自由不能为一个阶级独占,只有社会主义的到来,才有可能使工人得到自由。没有其他事物比这种分歧更危害革命的成功,阿尔芒那么热情去实现团结,我并不惊奇。我还钦佩他坚韧不拔的精神。只几天工夫,他把监狱变成了一个政治俱乐部;从早到晚,直至深夜,房间里、宿舍里开展讨论;讨论从来得不出结果,阿尔芒也从不灰心。可是一星期中有好几次,警察把他和他的同志抓走,拖着他们穿过监狱的走道;有时,他们的脑袋碰在石子路和楼梯台阶上。他从法庭回来面带笑容:“我们没有招供。”可是有一个晚上,我在房里等他,他回进房时,我又看到了他在《国民报》报馆大楼朝我转过来的那张脸。他坐下来一声不出,过了好一会儿说:
“艰苦吗?”
“里昂的那些人说了。”
“我们会坚持的。”
“那么严重吗?”我说。
“今天夜里将宣布成立临时政府。他们要您坚持到天亮。若要整个巴黎都造反,起义就不能后退一步。”
“我们拒不招供的效果全被他们破坏了。”
他嘴一抿,他羡慕我。我想跟他说:“不,这是不公正的,勇敢或是胆怯都没有我的份儿。”但是,这不是谈论他、谈论我的时候。我说:
他两手捧着头。他重新望着我时,他的脸恢复了镇静,但他的声音发颤。
“我过来了。”
“我们不应该自欺欺人。这场官司会打个没完!它不会产生我们所希望的效果。”
“您怎么过来的?”
“我给您提的建议您还记得吗?”我说。
他们高声欢呼,扑到箱子上。加尼埃看着我不胜诧异:
“记得。”
“我把弹药带来了,”我说。
他站起身,在房里踱来踱去,情绪激动。
加尼埃坐在他的同伴中间,前面是一大堆石头、树木、家具、铺路石、沙袋;他们在这堵墙上还插了带绿叶的树枝。他们手里忙着制造子弹,用衬衣破布和墙上撕下的告示纸做弹塞。每个人都赤裸着上身。
“我不愿意一个人走。”
分配我的任务是把粮食弹药送至圣梅里修道院,供给加尼埃。子弹在街上呼啸。有人企图在十字路口把我截住,他们对着我喊:“不要从那里走!那里路堵了!”我还是往前走。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帽子,另一颗打穿了我的肩膀,我还是继续奔跑。天空在我头顶掠过,大地在我马蹄下跳动。我奔跑,我摆脱了过去与未来,摆脱了自己和嘴里这股厌倦的味道。某个没有存在过的东西存在了:这座疯狂的城市,洒满热血,充满希望,是它的心在我胸中跳动。我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我是活的。”可是立刻又想道:“可能是最后一次活着了。”
“你们不可能都走。”
“明天宣布成立共和国,”阿尔芒说。
“为什么不可能?”
我在《国民报》的那幢楼里找到阿尔芒。他眼里闪烁喜悦的光芒。起义者占领了半座城市;他们攻占了兵营和弹药库。政府决心动用军队,但是军队是否依然忠诚,却没有把握。共和派领袖即将组成一个临时政府,由拉斐德领导,国民自卫军会集合在他们的老上司麾下的。
三天还没有过完,阿尔芒找到了带领同志一齐逃离圣佩拉齐监狱的方法。朝院子的门对面,在挖一个地窖,到监狱来修理的工人告诉阿尔芒,这条地道通往隔壁的一个花园。大家决定打通试试。门口有一个看守,一部分犯人在院子里玩球,吸引他的注意,其他人则去挖地,修理声盖过了我们的锤子声。花了六天工夫,地道差不多挖通了,尚留薄薄一层地面挡住光线的透射。斯比内尔那次逃过了四月十三日的大逮捕,这天夜里将带着武器和梯子,来接应我们翻过花园墙头;有二十四个犯人准备乘机越狱,潜往英国。但是我们中间要有一个人放弃获得自由的一切希望,在看守巡逻时,牺牲自己去把他扣住。
市民到处筑街垒;男人把树锯倒,横在马路中间;有的从屋里拖出铁床、桌椅;小孩和妇女挖起路面的石块,进行搬运;所有人都在唱歌。因戈尔施塔泰的农民也围着篝火唱歌。
“这由我来做,”我说。
“告诉阿尔芒,说我们占领了市郊,”加尼埃对我说,“要坚持多久,我们就坚持多久。”
“不。我们抽签决定,”阿尔芒说。
街垒开始增高了。从邻近每条街上拥过来带武器的人,加尼埃后面跟了一大群人,向波潘库街的兵营走去。我们攻上去,士兵没做多大抵抗便退却了。我们夺到一千二百支枪,分发给起义者。加尼埃率领他们到圣梅里修道院去,留在那里筑阵地。
“关二十年对我算得什么?”
在黑压压的人群上,可以看到他们的头盔、他们的刺刀闪闪发光。他们冲上莫尔朗码头,朝桥头扑来。加尼埃喊:“他们要冲我们!”抓起枪就放。立刻其他枪声从四面八方响了起来,乱枪声中有一声高喊:“筑街垒!拿起武器!”
“不是这么个问题。”
“龙骑兵!”
“我知道,”我说,“您以为我可以比别人做出更大贡献,您错了。”
我默不作声打量他。像在每个黑夜,像在每个白天,他害怕,这个我知道,他害怕死神毫不留情扑到他身上,把他变成一堆尘土。
“您已经为我们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行。”
“但是我会不会继续做出贡献,这就难说了。把我留在这里吧。我在这里不错。”
“一切准备就绪,”我说,“老百姓成熟了,可以暴动了。但是,阿尔芒要您自个儿发信号。”
我们面对面坐在他的牢房里,他瞧着我,这四年来他还没有对我这样认真瞧过。今天在他看来,理解我还是有必要的。
我钻入人群。我在前一夜计划时确定的那个地点找到加尼埃;他挎了一支长枪;他身后几条路上挤满了脸色阴沉的人,其中许多人带着枪。
“为什么振作不起来?”
“这里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您去找加尼埃,告诉他自己发信号。再到《国民报》馆来找我。我尽量去把共和派领袖召集来。”
我笑了:
我们又等了一会儿,他突然说:
“这是慢慢来的。六百年……您知道这要多少天?”
“是的,”阿尔芒说,“军队和保安警察害怕红旗。群众感到风向要转。”
他没有笑。
“您认为这样吗?”
“六百年后我还会继续斗争。您以为今天世界上要做的事比以前少吗?”
“这是阴谋,这是背叛,”斯比内尔气得说话也结巴了,“他们要吓唬老百姓。”
“世界上难道还有什么事要做的吗?”
大家等待着,没有人知道到底会出什么事。突然看到一个人骑马奔来,全身穿黑,举一面红旗,旗上一顶弗里吉亚帽<a id="jzyy_1_80" href="#jz_1_80"><sup>(5)</sup></a>;引起一阵喧嚣,群众面面相觑,迟疑不决,有几个声音喊:“不要红旗!”
这一次他笑了:
“现在快出事了,”斯比内尔说。
“我觉得是有的。”
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搜索,但是一张脸也分不清楚。
“说实在的,”我说,“您为什么那么盼望自由?”
“加尼埃在那里,在桥头上,”阿尔芒说。
“我爱阳光灿烂,”他热情洋溢地说,“我爱河流与大海。人心中蕴育的这些神奇的力量,您能同意人家扼杀吗?”
在奥斯特里茨桥前,队伍停了下来。讲台已经布置好了,拉斐德登台发表一篇演说。他谈到我们正要安葬入土的拉马克将军。有些人在他之后也讲了话;但是没有人关心这些演说、关心这个死了的军人。
“人有了这些力量干什么用?”
走到巴士底广场,我们看到综合工科大学学生朝我们飞奔而来,披头散发,衣衫凌乱;他们不顾禁令私自跑了出来。群众开始大叫:“大学万岁!共和国万岁!”在灵柩前开道的乐队奏起《马赛曲》,传说第十二团的一位军官刚才对学生说:“我是共和派。”辗转相传,整个队伍都听说了这条消息。“军队跟我们在一起。”
“管它干什么用!可以干一切愿意干的事,首先应该把这些力量解放出来。”
灵车由六个青年牵引,由拉斐德执绋;一万名保安警察排成两队跟在后面。政府在沿途布置了岗哨;这种炫耀力量的做法不但没有安定民心,反使暴动更有一触即发之势。街道、窗台、树杈、屋顶上挤满了人;阳台上悬着意大利旗、德国旗、波兰旗,提醒人们世界上还有法国政府没能打倒的暴君。人民一边走,一边高唱革命歌曲。阿尔芒在唱,还有我从霍乱中救出来的斯比内尔也在唱。一看到龙骑兵,个个怒火中烧,随手扳下树枝、捡起石头作为武器使用。我们经过旺多姆广场,拉车的青年离开了预定的路线,绕圆柱一圈。有一个人在我背后叫:“要把我们引向哪儿?”有一个声音回答:“引向共和国。”我想:这是把他们引向暴动,引向死亡。共和国对他们到底意味什么?他们准备战斗,但是获得的果实是什么呢?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但是他们相信,获得果实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因为他们准备好了要以血来换取。我说过:“里维尔算得什么?”但是安托纳觊觎的不是里维尔,而是自己的胜利;他为胜利而死,死得心满意足。他们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为了使自己的生命成为人的生命——不是蚂蚁,不是小飞虫,不是石堆。我们永远不让自己变成石头——火刑架在燃烧,他们在唱歌。玛丽亚纳说:“做一个普通人。”但是怎么做呢?我可以随着他们共同前进,我可不能随着他们共同冒生命的危险。
他俯身向着我:
上午十时,人权社和人民之友社的全体成员、医科学生、法科学生集合在路易十五广场<a id="jzyy_1_79" href="#jz_1_79"><sup>(4)</sup></a>。综合工科大学学生没有赴会;谣传他们接到了禁令。群众头上飘扬着幡旗、三色旗、绿叶树枝;每人手拿一个标志,有的挥动手中武器。天空阴暗,细雨濛濛;但是,希望的猩红色火焰燃烧着每个人的心。有一些事就要通过他们发生,这点他们深信不疑。他们还深信不疑自己能做出一些事来,手痉挛地抓着手枪的枪柄,为了证实这条信念不惜去死,为了证明自己的生命在世界上是有分量的,不惜去献出生命。
“人要自由,您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吗?”
我望着这张神经质的嘴、两道皱纹、痛苦的脸、严峻但有点不可捉摸的眼睛。他盯着天涯,天涯后面隐藏着汹涌咆哮的河流,高高的芦苇尖上摇摆着绿色花穂,鳄鱼睡在温暖的泥地里;他说:“应该让我感到我活着,即使为此死也甘心。”
我听到她的声音:“做一个人。”在他们眼里都有同样的信仰。我把手按在阿尔芒的臂上。
“您救了我一次生命,已经够了。”
“今天晚上,我听到您的声音了,”我说,“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对您说,请接受我的心意。这可能是最后一个晚上了;每个晚上都可能成为最后一个晚上。今天晚上,我愿意为您效劳,但是可能明天,我也没有什么可以献给您的了。”
加尼埃嘿地一笑:
阿尔芒眼睛紧紧盯住我,脸上惶恐不安;他好像突然发现了什么东西,是他从来不曾怀疑过、也有点令他害怕的东西。
“阿尔芒说得对,”我说,“我认识圣马尔索区的工人,让我来组织这次暴动。”
“我接受,”他说。
“没有我,你们照样办得很好。”
我仰身躺着,仰身躺在冰封的泥地上,躺在地板的板条上,躺在银色沙滩上,两眼凝望石头的天花板,感到灰色墙头围绕在我四周,在我四周围绕的是大海、平原和天涯的灰色墙头。在年代像世纪一样漫长、又像钟点一样短暂的世纪后,又是几年过去了;我凝望这块天花板,喊:“玛丽亚纳。”她说:“你会把我忘了。”顾不得世纪和钟点,我要把她活生生地留在身边;我凝望天花板,她的形象在我眼底逐渐清晰了;总是同样的形象:蓝色长裙、袒露的肩膀,这张与她本人不尽相同的肖像;我又试了试,一刹那我内心有样东西动了,可以说是一声微笑,但是瞬息即逝。又有什么用呢?她涂上香料保存在我心里,在这个冰冻的洞穴深处,依然像埋在她的坟墓里一样死。我闭上眼睛,但是即使在梦中我也不能逃逸;浓雾、幽灵、历险、幻变,都无法摆脱这种腐败的味道,这是我唾沫的味道、我思想的味道。
“要是你被人杀死,那就糟了,”斯比内尔说,“报纸怎么办?”
在我身后,门嘎嘎响了;有一只手触及我的肩膀,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他们的话;我想:“这早该来了。”他们碰了碰我赤裸的肩膀,说:“跟我们来。”棕榈树影子消失了。五十年后,还是一天后,还是一小时后,这最终总是要来的。“马车来了,先生。”应该睁开眼睛;有许多人在我周围,跟我说我自由了。
“不,”加尼埃说,“我一生中谈得够多了。这次我要战斗。”
我跟着他们穿过走廊,他们命令我做的事我都做了,我在几张证件上签了字,他们不由分说把一只包裹交到我手里,我接了过来。然后他们领我走到门前,门在我背后关上了。天空在下毛毛雨。潮水退了,岛的四周只看到一望无际的灰沙。我自由了。
“谈判该由你去,”阿尔芒说,“你说话比我有分量。福斯卡比我们更接近工人,他去守奥斯特里茨桥。”
我伸出一只脚,然后另一只脚。到哪儿去呢?在草原上,灯芯草发出嘶哑的呻吟,分泌出滴滴水珠,我朝天涯走一步,天涯往后退一步。我凝望天涯,踏上了堤岸;我看到他离我几米远,在向我伸手,在向我笑。他不再是个年轻人了。肩膀宽宽的,胡子浓浓的,显得和我一样年纪。他说:
这天夜里,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睡觉;大家沿着巴黎的环城道与各派进行联络。如果起义成功,应该努力说服拉斐德接受权力,唯有他的名字才具有号召群众的威望。加尼埃委托阿尔芒在事成后跟共和派领袖谈判;至于他自己,在奥斯特里茨桥旁布置了一些人后,自告奋勇去鼓动圣马尔索郊区暴动。
“我是来接您的。”
大家又七嘴八舌议论开了;他们说话响亮,眼睛闪光,声音发颤;在这些墙壁的另一面,在这个时刻,也有几百万人在议论,带着闪光的眼睛、发颤的声音;议论时,什么起义、共和国、法国、世界的前途都在那里,都掌握在他们手里,至少他们是这样想的;他们把人类命运紧紧贴在自己心上。全城围绕一座灵台吵吵嚷嚷,灵台上放着谁都不关心的拉马克将军<a id="jzyy_1_78" href="#jz_1_78"><sup>(3)</sup></a>的遗体。
他坚硬温暖的双手紧紧握住我的双手。河对岸有一团火光在闪耀,有一团火光在玛丽亚纳的眼里闪耀。阿尔芒抓住了我的胳膊,他在说话,他的声音是一团烈火。我跟着他;我伸出一只脚,然后另一只脚,心想:“又要开始了吗?又要继续了吗?继续开始,一天又一天,直至永远、永远?”
“恰恰相反……”
我跟着他沿一条路走;路永远是有的,是些哪儿都到达不了的路。然后,我们登上一辆驿车。阿尔芒继续在说话。十年过去了,占了他生命中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向我谈他的往事,我听着:话还是有着一种意义。总是同样的意义,同样的话。马在奔驰,窗外飘雪,这是冬天;四个季节,七种颜色;闭塞的空气中有一种旧皮子的气味。甚至这些气味我也是熟悉的。有的人下车了,有的人上车了;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多脸、这么多鼻子和嘴、这么多双眼睛。阿尔芒在说话。他谈到英国、大赦、返回法国,他为我的释放而奔波,还有当局最终同意释放我时他感到的喜悦。
“不管怎么样,共和派应该支持他们。”
“我老是盼望您越狱逃出来,”他说,“这对您并不难。”
“我怕他们不估计一下局势就行动,”布鲁索说。
“我没有试过,”我说。
“这是对的,”加尼埃说,“不要提口号,但是做好准备,人民要是行动,我们跟着他们行动。”
“啊!”
“当然会发生一些事的,”阿尔芒说,“要是你们不愿起义,至少要采取措施,万一起义爆发了知道该怎么办。”
他望我一眼,然后他的目光移开了。他没有向我提问题,又开始说话。他住在巴黎的一套小公寓里,和斯比内尔以及在英国认识的一个女人一起生活;他们打算让我住到他们那里。
我摇摇头。我怎么能当他们的顾问呢?在他们眼里,生与死意味着什么我知道吗?这是要由他们来决定的。如果生仅仅是为了不死,为什么要生呢?但是死是为了生,这不是荒唐的骗局吗?这不应该由我给他们选择。
我同意了,我问:
“您经验丰富,”他说,“您应该有个想法……”
“她是您的妻子?”
“我没有想法。”
“不,只是一个朋友,”他简略地说了一声。
他们乱哄哄地讨论了一会。阿尔芒低声问我:“您怎么想?”
当我们到达巴黎,整整一夜过去了。这是早晨,路上盖满了雪;这也是一个古老的景色;玛丽亚纳喜欢雪。她突然显得比我在洞穴深处时更接近、更无从追寻;在这个冬天的早晨,有一个位子是她的,而这个位子是空的。
“大量的血,还白流,”另一个说。
我们走上楼梯;十年来,五世纪来,事物没有变化;在他们头上总是有天花板,在他们周围总是有床、有桌子、有椅子,浅绿的或杏绿的,墙上还有护墙纸;在这四堵墙壁之间,他们一边生活,一边等待着死亡,他们沉湎在自己的人生梦中。犹如在牛棚里,奶牛带着它们绿色温暖的肚子、棕色的大眼睛,眼中饲草与绿色牧场的梦也不会有中断的一天。
“我们会冒大流血的风险,”有一个声音说。
“福斯卡!”
全室骚动了。
斯比内尔把我的手紧紧握在他手里,冲着我的脸笑;他还是老样子,只是相貌严峻了一点。也就在这一夜后,我便看到阿尔芒恢复了我所认识的原来面目。我觉得前一天才离开他们似的。
“即使起义不成只是一场暴动,也不是没有好处的,”加尼埃说,“每次反抗后,人民更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人民与政府之间的鸿沟也更深了。”
“洛拉来了,”阿尔芒对我说。
“谁知道呢?”阿尔芒说。
她向我严肃地看了一眼,向我伸出一只小巧的手,脸上不露笑容,神情紧张生硬。她已不年轻了,身材瘦小,深色大眼睛,肤色发青,黑色鬈发一绺绺垂在肩上,肩上披了一条长流苏头巾。
“既然没能协调我们的工作,”老布鲁索慢条斯理地说,“还不如放弃不干;这种条件下,发动一场真正的革命是不可能的。”
“你们饿了吧,”她说。
“应该做出决定。”
她在桌上摆了几大碗牛奶咖啡和一盆黄油烤面包。他们吃着,阿尔芒和斯比内尔谈笑风生,他们看到我显得十分高兴。我只是喝了几口咖啡,在牢内我已失去吃的习惯。我竭力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向他们微笑。但是,我这颗心像埋在冰冷的熔岩底下。
一阵静默后,加尼埃说:
“几天后将要为您举行一次宴会,”阿尔芒说。
“不知道我们的决定,他们怎么能做出他们的决定呢?”阿尔芒说,“不和他们商量,我们又能决定什么呢?”
“宴会?”
“我要参加高卢社和组织委员会,都没有成功,”我说,“我只是跟人民之友社有了接触,他们倾向于起义。但是他们还没做出任何决定。”
“将有几个主要工人组织的领袖出席;您是我们的一名英雄……四月十三日起义,十年牢房……今天您的名字具有的分量是您意料不到的。”
在《进步报》编辑室内,编辑委员会和人权社的各部主任集合在年老的布鲁索周围。他们都带着焦急的神情望着我。
“是么,”我说。
“怎么啦?”加尼埃说。
“想到为您举行宴会,您一定奇怪吧?”斯比内尔说。
阿尔芒和加尼埃对望了一眼,我转过眼睛。通过这一眼,他们彼此交换了内心迸发的喜悦感情;通过这些捷报的交流,他们找到了面对死亡的力量、生活的理由。我为什么要转过眼睛呢?斯比内尔他二十岁,热爱生活,我向他呼吁来救救我,我记起他炯炯有神的目光,青年人的口吃;我救了他,我在冰湖里游过去,把他驮到岸上,抱在怀里;我到印第安村子找寻玉米和肉,他一边笑,一边狼吞虎咽;腹部一个窟窿,太阳穴上一个窟窿;这个人会怎么样死呢?我内心迸不出一点喜悦的火星。
我摇摇头,但是他径自说下去:
“几乎可以肯定。”
“我来给您解释。”
“得救了?”
他说话总是滔滔不绝,带点儿结巴。他开始向我说明,现在大家已经放弃了起义的战术,把暴力行动留待革命真正爆发的那天使用。目前试图做的事是实现工人阶级大团结,在伦敦的流亡者使他们认识到工人联合会的重要性。宴会是显示这种团结的良好机会,要让宴会在法国各地盛行起来。他说了好一会儿,不时转身向着洛拉,好似征求她的同意。她也点头。他说完时,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