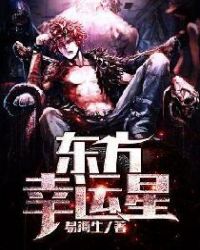A.S.拜厄特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爱米文学网aimiw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没怎么写……算是在写吧。但写得不顺利,我想可能是题材不对。”
“弗雷德丽卡,你别胡思乱想好吗?”
“在写作吗?”
“不行,我一直在思考,我必须思考。你也一样。”
“还行吧。开心,这是当然的。”
“不,我不思考。我感到很羞愧,但我算不上爱思考的人。”
“玩得开心吧?”她问。
可事实并非如此。他想跟她提起那幅《黄椅子》。那一团迷雾让他兴趣盎然,她也会很感兴趣。他转过身游走,动作很大,溅起一片水花。她紧跟着。在岸上,威尔基懒洋洋地躺着,双手托着腮,看着他们俩在水里嬉戏,自己笑了起来。威尔基的女朋友跑到水边,大声叫他们吃午饭,他们要吃午饭了。
“我鼻子上的皮肤都没脱。”亚历山大说。每次弗雷德丽卡缠着他说话时,他一会儿像正儿八经的大叔,一会儿像个顽童。他朝着船慢慢游过去,一翻身爬上船。他本想从船上再跳下来,结果,她始终跟着他,也想爬上船。他伸手拉了她一把,他们挨着坐在滚烫的木板上。
午饭很好吃,有香草煎蛋、熏火腿、巨大的猩红西红柿,感觉像微型南瓜,还有蒜泥胡椒黑橄榄,闪闪发光,皱巴巴,热乎乎。还有很多红葡萄酒,多数是旺吐谷红葡萄酒,很多好吃的硬皮面包。有气味很重、很新鲜的山羊奶酪,有卡瓦略甜瓜,瓤是玫瑰色的,瓜皮像传说中金绿色的毒蛇,克罗还特意往掏空的瓜壳里灌了粉红色的博姆德沃尼斯甜葡萄酒。当然,很多东西都进了沙子,旁边还有三四只黄蜂在嗡嗡叫,叮过各类肉和水果。弗雷德丽卡喝了很多酒,什么话也没说,而是一个个盯着这群人看,充满好奇地看着这些人懒洋洋地躺在沙滩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她也没太在意他们在聊什么。她的心思都在亚历山大身上。他躺在阳光下,靠近罗斯夫人和马修·克罗,但不靠近弗雷德丽卡,他似乎专注听人家聊天,主要是霍奇基斯、威尔基和克罗在说话,他们的话题是颜色的认知和表达,霍奇基斯正在写一篇关于色彩审美的文章,威尔基也曾用彩虹太阳镜做过关于颜色的实验。此时,威尔基正通过罂粟红太阳镜,盯着凡·高画过的渔船和奶油色的大海和天空,弗雷德丽卡觉得这副眼镜很别扭,不过,她真希望自己有勇气向他借过来戴一下,她也想戴着这副眼镜看看这里的一切。
黑一块红一块的头颅笑开了:“他们提醒过。晒了几个月才变成这样。我有阵日子晒得黑乎乎,很光滑。然后就开始脱皮。我本以为已经结束了。这样子太恐怖,吓着你了,对不起。”
霍奇基斯和威尔基聊到颜色的本质。霍奇基斯说话的腔调让弗雷德丽卡很不高兴,他说话总带着牛津腔,爱省略,也常用多余的代词。他说话的声音就像一个体弱多病的人,但他的身材却十分壮硕。他说他一直在读维特根斯坦38的笔记,而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生前一直在研究颜色的个人体验和普世意义之间的关系。他研究过颜色数学,认为饱和的红色或者黄色,就类似于圆或者斜边上的正方形。克罗说,凡·高时代的象征主义者主张世界存在普遍的颜色语言,那是世界的主要语言之一,颜色有神圣的字母和形式。差不多吧,霍奇基斯说,维特根斯坦曾自问过是否可能建立颜色自然史,就像植物自然史,然后又自答道,和植物自然史不同,颜色自然史超越时间限制。亚历山大说,在凡·高用法语写的信中,颜色形容词和它们所修饰的名词极少是匹配的。因此,黄色和紫色、蓝色和橙色、红色和绿色,这些颜色比名词所代表的事物更真实,那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永久形式,不属于这个由卷心菜和梨构成的现实世界。威尔基说,心理学家知道,颜色都有一定的心理作用,红色、橙色和黄色,可以提高肌肉张力,提高肾上腺素流量;蓝色和绿色可以降低心跳频率和降低体温。接着,他们的话题转换到颜色映射。
“你晒过头了。没人提醒你吗?你的肤色很奇怪。”
克罗说,普鲁斯特写过一段很古怪的话,他把字母和不同颜色联系起来,说“i”代表红色,在杰拉尔·德·奈瓦尔的诗歌《西尔维,真正的烈火姑娘》中就是这样。
亚历山大的脸舒展开,可能是因为高兴。为了掩盖这个变化,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