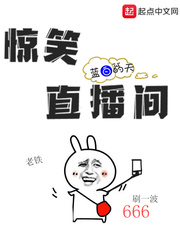第8节 (第5/5页)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爱米文学网aimiw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不是没想起来,”安布罗修说道,“您明白的,少爷。”
“流浪汉,你就一点也不在乎?”奇斯帕斯说道,不再笑了,但刮得精光的脸上仍保持着一丝笑意,神态中仍有一种不自在的样子,并且越来越不自在,小萨,而且又出现了不安的意味,“老头子去世这么多月,你就没想过问一下他留下的生意?”
“我不明白,”圣地亚哥说道,“你不是说很敬重他吗?你不是说他也很看重你吗?他肯定会帮助你,你怎么没想到?”
“那么就赶快把苦药拿出来吧,”圣地亚哥说道,“我要在喝汤前吃下去。”
“正是因为我敬重您爸爸,我才不想使他为难,”安布罗修说道,“您想想,他是什么人,我又是什么人,少爷?我难道能对他讲我是逃回来的?说我是小偷,警察局正在找我,因为我卖了一辆不属于我的车?”
奇斯帕斯又笑起来,但此时有些造作了。他一面笑,眼中一面迸出不自然的火花。小萨,他眼中闪着不安的光芒,连叫两声:唉,瘦子,你这个流浪汉!唉,瘦子,你这个流浪汉!圣地亚哥回想:其实我那时已经不发疯了,不再六亲不认,不再有变态心理,不再是共产党了。他回想:奇斯帕斯声音中有某种亲热的意味,也有某种模棱两可的意味,怎么理解都可以。小萨,他叫你瘦子,叫你流浪汉。
“你原先不是对他比对我更信任吗?是不是?”圣地亚哥说道。
“我知道你一听见生意这两个字就浑身起鸡皮疙瘩,流浪汉,”奇斯帕斯笑了,“但这次你是躲不过去的,一刻也躲不掉。我带你到这儿来看看辣味菜和冷啤酒能不能使你强吞下这剂苦药。”
“一个人的处境再倒霉,也有自己的自尊心,”安布罗修说道,“堂费尔民对我的观感很好,我却落了魄,倒了霉。您瞧。”
“我们要谈生意?”圣地亚哥说道,“我想你不至于建议我跟你一道干吧?你可别在吃这顿午饭的时候扫我的兴。”
“可你为什么对我说出来了呢?”圣地亚哥说道,“你把偷车的事告诉了我,为什么不感到难为情呢?”
“甜食我替你点,”侍者拿着单子离去后,奇斯帕斯说道,“奶白薄饼。谈完生意,吃这种甜食最好没有了。”
“可能因为现在我已经没有羞耻心了。”安布罗修说道,“可那时候还有。再说,您到底不是您爸爸呀,少爷。”
兄弟二人来到铁掌俱乐部的瑞典餐厅。侍者和领班都认得奇斯帕斯,直呼其名,开了几句玩笑就围在他身边转,既热情又殷勤。小萨,奇斯帕斯要你尝尝草莓鸡尾酒:瘦子,这是这家餐厅的特色风味,又甜又烈。二人在一张能看到堤岸的桌子旁坐了下来,看得见咆哮的大海和布满乌云的冬日天空。小萨,奇斯帕斯劝你第一道菜要一盘利马风味汤,第二道菜要辣子鸡羹或鸭肉米饭。
伊蒂帕雅支付的四百索尔早就用光了,到达利马的三天里,安布罗修一口东西没吃。他远离市中心,到处流浪,每次从远处看见警察总要吓得浑身发冷。他想着熟人的名字,一面想一面排除。鲁多维柯,不;伊波利托,可能还在外地,即使回来了,也很可能跟鲁多维柯在一起工作,因此,伊波利托,甭想,没门儿。他没有想念阿玛莉娅,没有想念阿玛莉塔·奥登希娅,也没有想念普卡尔帕,心里装的全是警察局、吃饭和抽烟。
“你找了个理想的小巢,瘦子,”奇斯帕斯观察着桌子、书橱、巴杜盖睡觉的粗麻布说道,“这房子对你和安娜这样到处为家的人倒很合适。”
“您瞧,为了吃饭,我从不敢乞讨,”安布罗修说道,“可为了抽烟,我乞讨了。”
同奇斯帕斯的那次谈话是在堂费尔民去世后很久,是在圣地亚哥从《纪事报》地方版调到社论组一个星期之后,小萨,也是在安娜丢掉医院工作的前几天。报社给你加了五百索尔的工资,把工作时间从晚上改为早晨,于是你几乎再没见到卡利托斯了,小萨。一天,你遇到奇斯帕斯从索伊拉太太家中走出来,二人在人行道上谈了一会儿。超级学者,我们明天一起吃午饭,好吗?当然,奇斯帕斯。当天下午你想了很久,但并不觉得奇怪。有许久没谈话了,他想说些什么?第二天中午一过,奇斯帕斯就到窄小胡同来接圣地亚哥了。这是他第一次来,小萨,他进到胡同里来了,你透过窗子看着他犹疑着敲了敲德国女人家的门。他穿着米色西服,还穿了坎肩,黄色衬衣的领子很高。那德国女人从上到下贪婪地打量了他一眼,指着你家的门说:是那扇“C”字的门。小萨,于是奇斯帕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踏进了你那坐落在窄小胡同的家门。他在圣地亚哥的肩上拍了一下:你好,超级学者。接着带着自然的笑容参观了那两间小屋。
他实在忍不住了,就在街上随便拉住一个人,找人要烟抽。他什么工作都干过,只要不是固定的工作,不需要出示身份证。他在波尔维尼尔小区卸过卡车,烧过垃圾,为凯罗里马戏团的动物捕捉过猫和狗,掏过阴沟,甚至给磨刀人当过助手。有时在卡亚俄港的码头顶替正式装卸工干几个小时,虽说佣金被抽去很多,但总够吃两三天饭。一天,有人告诉他,奥德里亚分子需要贴标语的人,他去了,在市中心街道的墙上整整刷了一夜糨糊,但是只挣得酒饭。这几个月中,他到处流浪,忍饥挨饿,东奔西走,有时干上一两天临时工。有一天,他认识了潘克拉斯。起初他在帕拉达市场睡觉,卡车下、沟渠里、仓库的麻袋上都是他睡觉的地方。躲在睡在一起的众多乞丐、流浪汉中,他感到安全。但是有一夜,他听到不时地有警察巡逻队过来查证件,于是迁到贫民区去睡了。他知道所有的贫民区,在这个贫民区睡一夜,又到另一个贫民区睡一夜。就这样,他在佩尔拉贫民区遇到了潘克拉斯,就在该区住了下来。潘克拉斯单身一人,在自己的破屋子里给他腾了一块地方。
小萨,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要说的?圣地亚哥回想:啊,还有同奇斯帕斯的那次谈话,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可谈了。堂费尔民去世后,安娜和圣地亚哥开始每星期天同索伊拉太太吃午饭,在家里也能见到奇斯帕斯和卡丽、波佩耶和蒂蒂。但是后来索伊拉太太到欧洲旅行去了,家庭午餐也就中断了。圣地亚哥回想:以后就没再恢复,将来也不会恢复了。索伊拉太太是同埃丽阿娜姨妈一同去欧洲的。埃丽阿娜姨妈想把大女儿送到瑞士的一所公学就读,顺便到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玩两个月。晚点儿有什么关系,安布罗修?祝你健康,安布罗修。索伊拉太太回国时不那么颓唐了,被欧洲夏日的太阳晒黑了,手里拎着礼物,口中趣闻不绝。小萨,不到一年的时间,她就恢复了正常,恢复了繁忙的社交活动,打牌、访友、看电视剧、开茶会。安娜和圣地亚哥经常来看她,每月至少一次。她也留二人吃饭。从此母亲与儿媳的关系虽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很客气、友好,当然还不是那么亲热。现在索伊拉太太以一种有分寸、和蔼的态度,以一种无可奈何的温柔、亲热的态度对待安娜了。小萨,索伊拉太太没忘记给安娜分一份从欧洲带来的纪念品,也送了安娜礼物。圣地亚哥回想:一条西班牙披肩、一件意大利绸衬衣。过生日或逢结婚周年的时候,安娜和圣地亚哥在客人们到来之前很早就过来,匆匆地拥抱索伊拉太太。有时波佩耶和蒂蒂来到窄小胡同跟二人聊天或带他们出去兜风。奇斯帕斯和卡丽却从来没来过,小萨,但在举行南美洲足球锦标赛的时候,奇斯帕斯给你送来了一张头等座的长期票。你经济拮据,就把长期票平价卖了。圣地亚哥回想:我们终于找到了和睦相处的方式,小萨,那就是不即不离,互相微笑,也开开玩笑。可我不能太晚啊,少爷,请您原谅。啊!是太晚了。
“很长时间以来,这是第一个待我好的人,”安布罗修说道,“他既不了解我,又对我无所求。我跟您说,那黑人真是个心地慈善的人。”
“我不是想扫您的兴,绝对不是,”安布罗修说道,“是因为实在太晚了,少爷。”
潘克拉斯在狗场工作了好几年,二人交上朋友后,潘克拉斯把他带到狗场管理员面前。管理员说:不行,没有空缺。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管理员把他找了去。需要看证件:选民证、服役证、出生证,都没有?安布罗修只得撒了个谎:全丢失了。啊,那就别谈了,没有证件是不能工作的。潘克拉斯后来对他说:你别发傻了,谁还会记得偷车的事?快把证件送去吧。安布罗修还是害怕:算了吧,潘克拉斯。于是他又偷偷摸摸地做起临时工来。在那段时间里,我回了故乡钦恰一次,少爷,那也是最后一次。您问我干什么去?我想重新搞几个证件,让某个神父用另一个名字再给我做一次洗礼;也是出于好奇,想看看现在的故乡什么样了。安布罗修对那次回乡之行感到很后悔。那天一大早,他同潘克拉斯一道离开佩尔拉贫民区,二人在五月二日广场分手。安布罗修沿着哥尔梅纳路走到大学公园,打听了车价,买了十点那班车的车票。还有时间喝杯牛奶咖啡,溜达溜达,他在依基托斯路的商店橱窗前看了又看,计算着是不是要买件衬衣,好在回到钦恰时比十五年前离开时像样,但他只有一百索尔,买不成了。他买了一卷薄荷糖。一路上,牙龈、鼻子和上颌都感到这糖的清凉香味,但是胃里咕咕直叫。他想:我认识的人看到我这副样子会怎样讲呢?沧海桑田,人的变化真够大,有的死了,有的搬走了,也许连城市都变得认不出来了呢。但是当汽车在中心广场停下来时,一切仍都认得出来,虽然都显得小了、矮了。空气中的气味、长椅、房顶的颜色、教堂前面的人行道上那三角地带的花砖,都同以前一样。他感到一阵难过、头昏,也感到羞愧,仿佛时间并没有流逝,他没离开过钦恰。拐过街角就是钦恰运输公司的办公室,他的司机生涯就是从那儿开始的。他坐在长椅上一面吸烟一面观察。是的,有些方面变了:人们的面孔变了。他热切地望着过往的男男女女,当看到一个人头戴草帽、光着脚,以杖探路、疲惫地走过来时,他感到心脏急剧地跳动起来。啊,那是瞎子罗哈斯。但并不是他,而是一个患有白癜风的年轻盲人。盲人走到一棵棕榈树下蹲了下来。安布罗修站起身,迈动脚步,到了贫民区,只见有些街道铺上了沥青,盖起了几幢带小花园的矮小房子,花园里的草枯萎了。街道尽头是通往格罗修·普拉多村的道路,路旁是田地,也盖起了一片茅舍。他在贫民区那尘土飞扬的小路上来回走了好几趟,没认出个个熟人的面孔。接着他又来到了公墓,心想,黑妈妈的坟也许就在佩尔佩铎墓的旁边。但他没有找到,他不敢去问守墓人黑妈妈到底埋在何处。黄昏时分,他回到市中心,心灰意懒,饥肠辘辘,把重新洗礼和取得证件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在“我的祖国”咖啡餐厅里(现在改名为“胜利”,招待顾客的不再是堂罗慕罗,而是两个女人),他坐在临街的桌子旁吃了洋葱烤肉,一边吃一边望着大街,想认出某些熟人的面孔,但一个也没有认出。他想起了去利马的前夜,特里福尔修同他在黑暗中走的时候对他说的话:我人在钦恰,又好像不在钦恰;我认出了一切,又好像什么也认不出来。现在,安布罗修才理解这些话的含义。他又在另外几个区游荡了一会儿,看到了何塞·帕尔多中学、圣何塞医院、市立剧院。市场现代化了。一切都同以前一样,但显得小了;一切都同以前一样,但显得矮了。只有人不一样。我很后悔去这一趟,少爷,我当天晚上就回到了利马,发誓再也不去了。我在利马倒了霉,可在钦恰,不但感到倒霉,还感到自己老了,少爷。等狂犬病过去,你在狗场的工作是不是也就结束了,安布罗修?是的,少爷。那你怎么办?后来狗场管理员又命潘克拉斯把我找了去,对我说:好吧,你可以帮我们干几天,没有证件也行。等狂犬病过去了,在这之前干什么,我就还去干什么呗。我可以到处找工作。也许不久后再发生狂犬病,狗场还会把我找去。然后再到处流浪,到处找工作。对了,再然后,就去见上帝。您说对吧,少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