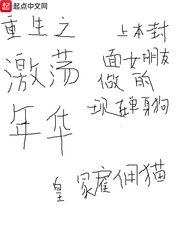加·泽文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爱米文学网aimiw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好啊,真是谢天谢地。我最讨厌自带‘同志雷达’的人。这其实就是一种歧视,但是有了这个搞笑的词,大家就觉得这件事很搞笑。你知道自带‘同志雷达’的都是什么人吗?老顽固。”
“也许我们可以发起一项‘反对同志雷达’的运动?”你说。
“来吧。”阿尔奇说。
“其实没有你想象得那么难,”你说,“你在显眼的地方发表几篇跨页社论,或者任何一个愿意让你发表文章的地方。开头几篇可以写得幽默些,引起人们的关注。要是你运气好,人们会开始就这个话题发表博文。这时你给当地电视台打电话,他们可能不会理你,因此你需要物色一名对同性恋不错的政治人物——可以是地方议会议员,代表南海滩或者其他有大量同性恋选民的地区——让他引入一项立法,哪怕只是针对‘常见的仇视同性恋言论,尤其是‘同志雷达’一词的使用’发表一份声明也行。你上网找个论坛,集结一群有同样想法的人,让他们举着标语出来游行,反对同志雷达。”
“‘同志雷达’,滚出去!”阿尔奇建议道,“滚出去?”
“好吧……”你说着,皱起鼻子笑了笑,“要么还是想个更好的口号?”
“我再好好想想。”阿尔奇说。
“立法听证会上,你找个上镜的高中生来讲故事,就说他或她为‘同志雷达’这个词受了不小的负面影响。这时你再给新闻频道打电话,他们这次保准会来。等你集齐了政治人物、高中生和一群举着标语的群众,保准能让市长或者市议会负责人满脸尴尬地翻来覆去地说同志雷达这个词——”
阿尔奇装出一本正经的声音,老古板似的说道:“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同——志——雷——达’?”
“没错。我是说,这可是绝佳的素材。你说他们怎么能跟我们抗衡?”
“即使你不能让‘同志雷达’这个词被正式禁用——你本来也没打算那么做,因为没人能禁用某一个词——等你做完这一切,至少提高了人们对这个词的认识,哪怕只有百分之一。而且可能有些人在说‘同志雷达’之前会停顿一下。”
“他们会停顿一下,说:‘好吧,我知道这样说政治不正确……’然后他们还是会说这个词。”阿尔奇说。
“不过你想想,虽然只是短短一句话,但这种禁令会让你觉得自己多么受人认可啊。那已经赢了!”
“我不确定这究竟会让人情绪低落还是精神振奋。”阿尔奇说。
“绝对是精神振奋,”你说,“虽然只是微不足道的努力,但毕竟聚少成多。”
“你说这件事当中,政治还是媒体的成分大?”阿尔奇开玩笑地说。
“媒体,”你说,然后又想了想,“也许它们的本质其实是一样的。”
“嗯,他们如今就是这样教导实习生的吗?”阿尔奇问。
“我已经不是实习生了,”你说,“顺便说一句,我刚入职的时候,那里甚至连一个知道什么是博客的人都没有。他们都太老了。”
“我明白,”阿尔奇说,“我办公室里有个岁数很大的律师,他已经问过我五遍怎么开关电脑。我想说,大哥,那不是有开关吗,没多难啊。”
阿尔奇把你送回你的公寓。你今年没有住在学校宿舍。你正要开门,议员忽然打了你的手机。“我在你家附近。”他说。
“怎么了?”你说。
“我想你可以向我介绍一下你的新家。”他说。
<b>假如你邀他过来,翻到第97页。</b>
<b><strike>假如你找个借口(“我在博卡拉顿”或者“我累了”),翻到第114页。</strike></b>
——97——
“过来吧。”你说。坦白地说,你搬到校外公寓住并且没找室友的原因之一就是你希望会发生这样的事。你已经搭好了舞台,你知道演员对戏剧的召唤毫无抵抗力。
“今晚我们没见到你。”他说。
离选举还有一个月,那天夜里在市政厅开会,你没去。
“我去约会了。”你说。
“哦,是吗?我应该吃醋吗?”
“不。”你说着,脱掉了衬衫。
“很好,”他说,“你去约会这很好。我希望你遇见个好人。”
你脱掉了短裙。
“你真漂亮。”他说。他走进你的卫生间,打开了水龙头。
你把头发绾在头顶。为了准备与阿尔奇的约会,你给头发做了造型,你不想弄乱。
“大家注意到了你今晚没来。”他高声说。
你打开电视。电视上在重播《谁会成为百万富翁》。
屏幕上的问题是:
在罗马天主教廷拒绝了亨利八世的休妻请求之后,亨利八世与教廷决裂,迎娶了哪个女人?
A.安妮·博林
B.简·西摩
C.克里维斯的安妮
D.阿拉贡的凯瑟琳
“克里维斯的安妮。”他走出卫生间,说道。
答案是安妮·博林。
“可恶,”他说,“我总把那两个安妮搞混。”
你把一只枕头放在地上。你双膝跪地,他打开了裤子拉链。
<b>假如你继续与他私会,翻到第99页。</b>
<b><strike>假如你告诉他一切都结束了,翻到第166页。</strike></b>
——99——
你又像过去一样与议员私会。每星期一次,有时两次。这是个坏习惯,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觉得自己成了议员的垃圾桶,或是他的行李箱。你觉得自己不过像个物件,感受不到爱。
你在考虑辞职,尽管你发自内心地喜爱这份工作,尽管你擅长这份工作,尽管工作能力是你自信心的来源。你喜欢做阿维娃,什么东西都能调查清楚的女生。
倘若你离开这份工作,或许就能够离开他。
<b>假如你不辞职,翻到第100页。</b>
<b><strike>假如你辞职,翻到第173页。</strike></b>
——100——
你知道自己应该辞职,但你决定等到选举结束。不过,你已经行动起来,整理了一份新的简历,试探着联系其他职位。
十一月,他得以连任。
他没有离婚,但你原本就没抱希望。
<b>翻到下一页。</b>
——101——
你有段时间没和他见面了,你甚至连想都不想他。
你决定在一月离职。那是你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看起来是个合适的离职理由。
你找到主管,告诉她你会做到月底,与新员工交接。“真遗憾你要走了。我们真的很喜欢与你共事,”她说,“不知我有没有机会说服你留下来?”
“没有。”你说。
她请你到楼下吃酸奶冰激凌。法鲁克说:“你好啊,阿维娃!”
“她要离职了。”主管说。
“没人比我更努力工作……只有阿维娃和议员先生除外。”法鲁克说。他送给你和主管一盘免费的果仁蜜饼。
“我必须得说,”你的主管说,“你第一天上班时,我没想到你会这样成功。你让我认识到了自己对实习生抱的一些偏见。”
你知道她是好意,但你依然觉得恼火。“为什么?”你说,“因为你不喜欢我的穿着?”
“是的。这样说不太好听,我觉得。我们时不时就会遇到一种女生,长着一张漂亮脸蛋,看过几部《风起云涌》之类的电影,就想加入政坛凑热闹。可一旦她们发现这里的工作有多无聊,她们就不想工作了。”
“好吧,或许假如你能让她们觉得更有归属感,她们就想工作了。”你说。
主管点点头:“我是个浑蛋。千真万确的浑蛋。”
她举起自己的冰茶,你用健怡可乐和她碰了碰杯。
<b>翻到下一页。</b>
——103——
一月底,距你离职还有一个星期时,他从华盛顿回来小住,他问你要不要“玩玩”。他这么说话像你过去那间宿舍里住的小年轻。你并不想“玩玩”,但你还是随他去了。
你坐在他车里——你离职的唯一目的就是不再坐进他的车——可你此刻还是在这儿!你坐在他车里,心里想着胡迪尼<a id="z20" href="#z20"><sup>【20】</sup></a>。你最近读了一本关于胡迪尼的书,你不禁想,与上司偷情和穿着约束衣被铁链捆住沉入水底有几分相似。你觉得要从这段感情里脱身,你必须是个情感世界的胡迪尼才行。
这是你自找的。
你只能怪自己。
纯粹是为了探讨,你还可以怪谁呢?
A.议员先生。
B.你父亲,你深爱的父亲,以为你不知道他有情人的父亲。
C.议员办公室那个第一天上班就惹你哭鼻子的主管。
D.对你的生活处处指手画脚的母亲。
E.你十五岁时的男朋友。
F.你那对让一切都带上了情色意味的胸。
不,你作出了决定,以上这些都不该怪。原因在我自己。
将来你也会有属于自己的实习生。哪怕只是想象自己与他们其中的某一个上床,你都觉得这是丧失理智、大错特错的行为。然而此时此刻,你却坐在议员的副驾驶位上。他正在等红灯,你暗自思量,或许我应该直接开门下车。没人拦着你,阿维娃·格罗斯曼。你是自由之身。你的确已经成年,但你依然可以打电话让母亲来接你,无论她在做什么,她一定都会来。你把手放在车门上,想等红灯变绿、汽车发动时把车门猛然推开。
“你怎么这么安静?”他问。
因为,你心想,我也有你不了解的内心世界。但这样的话若是说出口,就会违悖你们的相处原则。你们的关系不是这种基调。倘若他想要个内心世界丰富的人,他大可回家找他老婆。你是他的垃圾填埋场,你是他的高尔夫球袋。
“累了,”你说,“上课,上班。”
他把音乐的音量调高。他喜欢嘻哈音乐,可总像是在装样子。他向来执著于与年轻人打成一片。
那首歌是流浪者乐团唱的《杰克逊女士》。你以前没听过。歌曲的开头,那个第一视角的旁白/歌手在向女孩的母亲道歉,说自己不该那样对待她的女儿。你实在想不出比这更让你反感的歌曲了。
“能不能听点儿别的?”你问。
“听听看嘛,”他说,“说真的,阿维娃,你应该对嘻哈音乐态度开放些。嘻哈才是未来的趋势。”
“好。”你说。
“流浪者乐团就是沃尔特·惠特曼。流浪者乐团就是——”
你听见一阵玻璃破碎、金属挤压变形的声音。
车里的气囊弹了出来。
驾驶座旁的车窗玻璃裂了,透过玻璃往外看,外面的世界像是教堂彩绘玻璃窗上的超现实图案。你透过玻璃看见了椰子树和另一辆车的风挡玻璃,那是一辆淡粉色的凯迪拉克,一位老妇人的头耷拉着——可能已经死了。
“像彩绘玻璃。”你说。
“更像是立体主义。”他纠正道。
人们将会查清那名老妇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她的驾照三年前已被吊销,她的丈夫甚至并不知道她手里还有车钥匙。当他得知她去世的消息时,他会说:“她多么喜欢那辆车啊。”
议员扭伤了手腕。你的脖子受了点儿伤,没什么大碍,但眼下你还不知道。此时此刻,形势骇人。
“你没事吧?”他问。他的声音出奇地平静。
你有些头晕,但你知道必须尽快离开现场。你担心警察发现他与曾经的实习生有染,你想保护他不受牵涉。你认为他是个好人。不,你认为他是个优秀的议员,你不想让他卷入丑闻当中。
“我得走了。”你说。
“不,”他说,“你留在这儿。如果那个女人死了,警察一定会深入调查,你是我的证人。假如你现在离开,后来又被人查出你其实在场,这件事看上去就像是我们故意有所隐瞒。这是丑闻和犯罪的区别。丑闻总有平息的一天,如果犯罪,我的事业就彻底完了。警察来了以后,你就说你是实习生,我顺路送你回家。你大可不必心虚,因为这就是事实。”
你点点头。你的头沉甸甸、轻飘飘的。
“说一遍,阿维娃。”
<b><strike>假如你逃跑,翻到第110页。</strike></b>
<b>假如你留下,翻到第124页。</b>
——124——
“我是个实习生,”你说,“莱文议员顺路捎我回家。”
“我很抱歉,阿维娃。”议员说。
“为什么抱歉?”你昏昏沉沉地说,“是她撞上你的。这不怪你。”
“为即将发生的一切。”
你们等待警察到来。天上下起了雨。
<b>翻到下一页。</b>
——125——
你在一场暴雨之中。
雨水拍击着你,你的衣衫湿透了。
你的房子随水流漂走。
你的狗不在了,你却连感伤的时间都没有。
你的相册遗失、受损、被水浸透无法修补。
你的保险也不管用。
你紧紧扒住一张床垫。
你没有人可以求助。
你的家人和朋友在暴雨中消失无踪。
幸存下来的人对你满腔怒火——你竟敢活下来。
你觉得这场雨永无止息。
不过雨最终还是停了,雨停的时候,记者也随之而来。
记者们爱死这个故事了:暴风雨里床垫上的那个女孩。
“床垫上的那个女孩是谁?”
“她在哪里上学?”
“她在学校人缘好吗?”
“她怎么穿得这么少?”
“既然她要被冲到床垫上,她就该多穿些衣服!”
“她怎么这么不知好歹?”
“我听说床垫上那个女孩精神不正常。她跟踪暴雨。专门追着暴雨跑。”
“她是不是长期自卑啊?”
“我还以为暴雨看中的人会更瘦、更漂亮呢。”
“我自认为是个女权主义者,但你若执意在暴雨中抓着床垫不放,那么错只在你。”
“我的天啊,床垫女孩有个博客!”
“敬请关注对床垫女孩前男友的独家访谈!格罗斯曼‘向来非常缠人’。”
真奇怪,每个人都爱(痛恨)床垫上的女孩,但似乎没有一个人对那场暴雨感兴趣。
<b>翻到下一页。</b>
——127——
看这架势,人们仿佛永远也说不够床垫女孩的故事,但一场更大的暴雨来临,雨中带着更吸引人的元素,比如恐怖主义、世界末日、死亡、毁灭和骚乱。
于是他们便把你忘了,算是忘了吧。
<b><strike>假如你决定再也不出门,变成布·拉德利那样的隐居者,翻到第128页。</strike></b>
<b>假如你决定重建生活,翻到第132页。</b>
——132——
你继续自己的生活。你当然要继续。你还有什么选择呢?你起床。你梳头。你穿衣服。你化妆。你坚持吃沙拉。你与服务生闲谈。你对别人的目光报以微笑。你笑得太多。你想让人觉得你很友善。你去逛商场。你买了一件黑裙子。你买了卸妆水。你读杂志。你健身。你不上网。你读书。你吃腻了沙拉。你吃酸奶冰激凌。你与父亲说笑。你从不与他或任何人谈起发生的事。你经常自慰。你不给议员打电话。
你参加了祖父的葬礼,他是你父亲的父亲。你与他的关系不如外祖父那样亲近,但你还是哭了。他曾经送给你一个阿根廷的木偶。如今你一位祖父也没有了。你哭。你不停地哭。你怀疑自己甚至不是在为祖父而哭。
你来到犹太教堂的女卫生间。你走进隔间,听见两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在你后面走进卫生间。你听见她们往身上喷香水的声音。教堂的卫生间总堆得像个药妆店:除了香水,还有口香糖、发胶、唇膏、保湿霜、漱口水、发带、梳子。
“这个味道真好闻,”一个女人说,“这是什么香水?”
“我也不知道,”另一个女人说,“我没戴老花镜,但我觉得是其他香水的仿冒品。”
“不是仿冒的,”第一个女人说,“去年闹得很凶。雪莉——”
“哪个雪莉?”
“哈达萨·雪莉。哈达萨·雪莉说,教会使用仿冒香水很不道德,所以现在用的都是正品香水。”
“哈达萨·雪莉真是小题大做。”第一个女人说。
“但她办事很有一套,”第二个女人说,“还有,小点声。哈达萨·雪莉的耳朵灵着呢。”
“她今天没来,”第一个女人说。
“我发现了,”第二个女人说,“可怜的埃博·格罗斯曼。”
“你觉得埃博知道多少?”第二个女人说。埃博是你的祖父。这些女人不是你的亲戚,那她们一定是他的好友。不过她们也可能只是多管闲事的教会成员而已。
“他脑子已经糊涂了,”第一个女人说,“大家没把那件事告诉他。事情闹得太大了。”
“的确很大,”第一个女人应和道,“要是被他知道,保准要了他的命。”
你意识到她们的话题转移到了你身上。
你对于谈话的走向不再有丝毫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