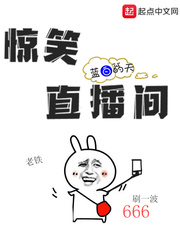加·泽文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爱米文学网aimiw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你走出隔间,来到她们两人之间。“能借我用一下吗?”你说着,拿起香水喷在身上,你看了看瓶子,“是祖·玛珑,”你告诉她们,“葡萄柚味。”
“哦,我们还在纳闷呢,”第一个女人说,“真好闻。”
“你还好吗,阿维娃?”第二个说。
“好极了。”你说。
你向她们微笑。你笑得过头了。
又过了一个学期,你大学毕业了。
你在相关领域申请工作——大部分是政治领域的工作,偶尔有些公共关系和非营利组织的工作。
你最有说服力的工作经验是议员那一份,但他的团队里没人肯给你写推荐信,原因不言而喻。
尽管如此,你依然满怀希望。
你二十一岁。
你重新润色了简历,看起来并不差。你说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你是优秀毕业生!你为一座大城市的众议员工作了两年,后来甚至成了领工资的员工,并且有自己的头衔——线上项目及专项调查。你曾写过一个点击率过百万的博客,但你不能把它现于人前。
住在纽约、洛杉矶、波士顿、奥斯汀、纳什维尔、西雅图、芝加哥的人不可能全都听说过阿维娃·格罗斯曼。这则新闻不可能传得那么广。这只是一则本地消息而已,就像你小时候,格洛丽亚·埃斯特凡和她的乐队“迈阿密之音”的巡演大巴出了车祸。这件事每天都出现在南佛罗里达的新闻中。这则新闻的确也曾在全国播出,但格洛丽亚·埃斯特凡的康复过程只是区域性地受人关注。
你递上去的工作申请几乎全部石沉大海。
终于有人给你打来了电话!是一个帮助世界儿童享受医疗保健机构的初级职位。
他们的总部在费城,与墨西哥的交流很多,他们非常看重你会说西班牙语这一点。
你与他们约定了电话面试,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你将飞到费城与这个团队面谈。
你幻想着在费城的新生活。你上网浏览冬季大衣。佛罗里达的商店有这些商品。住在一个有冬天的地方多好啊。住在一个没人听说过你的名字、没人知道你二十岁时犯下的错误(实事求是地说,是一连串错误)的地方,多好啊!
时值六月。你让妈妈离开了家,你端坐在卧室,等着电话铃在9:30响起。正值夏季,妈妈的学校放假了,她整天围着你转,就像苍蝇围着生肉打转。
电话铃没有响。
等到9:34,你开始担心自己是不是错过了电话,或是记错了时间。你重新查看邮件,核对细节。没错,是9:30。
<b><strike>假如你继续等待电话铃声响起,翻到第141页。</strike></b>
<b>假如你给他们打电话(面试官说过她会给你打来电话——但你才不在乎自己是不是表现得“太过主动”呢!),翻到第143页。</b>
——143——
电话接通的第一声,面试官就接起了电话。
“哦,阿维娃,”她说,“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你听得出她说的不是面试的事。
“我们还是另作了决定。”她说。
通常情况下你不会追问细节。但你已经受够了被人冷落,于是你说:“您能不能和我说实话?究竟出了什么事?我对这次面试的预感不错。”
面试官停顿了一下:“是这样,阿维娃,我们在网上搜了一下你的名字,然后就看到了你和那位国会众议员的事情。我本人并不介意,但我的上司认为,既然我们是个非营利性组织,就格外需要清白的人。这是他说的,不是我。但事实就是,我们的存亡全靠捐款,而有些人在性行为这方面超级古板、守旧。我为你争取过机会,我真的争取过。你很优秀,我相信你会找到其他合适的岗位的。”
“谢谢您的坦诚。”你说完,挂断了电话。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给你打电话的人都没有。
在费城、底特律、圣地亚哥,即便那里没人听说过阿维娃·格罗斯曼的丑闻,只要他们一搜你的名字,就能把关于那件事的每个丑恶细节都找出来。你早该知道的,网上搜索是你的强项。
想知道基西米河不为人知的过去吗?想知道哪位地方议会的议员仇视同性恋吗?想知道那个佛罗里达的蠢丫头与有家室的国会众议员肛交——因为他不肯插入她的阴道——的事情吗?
只要鼠标一点,你的耻辱便大白于天下。每个人的耻辱都是如此,但这对你并无益处。你高中时读过《红字》,你意识到这正是互联网的作用。故事伊始曾有一幕,海丝特·白兰站在镇中心的广场上示众了一个下午。或许只有三四个小时,但无论时间长短,对她而言都难以承受。
你将永远站在那个市镇广场上。
你至死都将佩戴着那个“A”。
你思考自己能做什么。
你没有任何选择。
<b>翻到下一页。</b>
——145——
你患了抑郁症。
你把每一本《哈利·波特》读了又读。
你泡在父母的游泳池里。
你读遍了儿时书架上的书籍。
你读了一套名叫《惊险岔路口》的书,你小时候很喜欢这套书。尽管你早已过了目标读者的年纪,但那个夏天你读得如痴如醉。这些书的结构就是,读到一章结尾,你作出选择,翻到相应的那一页。你不禁想到这些书和生活很像。
唯一不同的是,在《惊险岔路口》中,你可以走回头路,假如你不喜欢故事的发展,或者只是想知道其他可能的结局,你还可以重新选择。你也想这样做,但是你做不到。生活的脚步一刻不停。你要么翻到下一页,要么停止阅读。假如你停止阅读,故事将就此结束。
即使是在小时候,你也很清楚《惊险岔路口》的故事都是为了塑造良好的品格。打个比方,你最喜欢的故事之一《田径明星!》当中,一位田径运动员为了是否服用兴奋剂而犹豫不决。假如你选择服药,你将在一段时间里接连获胜,但后来就会发生糟糕的事情。你终将为自己糟糕的选择自食苦果。
你想到倘若你的生活也是一则《惊险岔路口》故事——暂且叫它《实习生!》——眼下就该是“全文完”的时候。你作出了许多糊涂的选择,足以让故事落得个糟糕的结局。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回到故事的开头,重新开始。在你这里行不通,因为你是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惊险岔路口》中的角色。
《惊险岔路口》的棘手之处就在于,如果你不作出任何错误的决定,故事就会十分乏味。假如一切顺利,你又总是作出正确的选择,故事很快就会结束。
你很好奇议员有没有读过《惊险岔路口》。或许他年纪太大了,但你相信他会读得津津有味,他会读懂那些故事其实是对生活的暗喻。
<b>假如你给他打电话,翻到第147页。</b>
<b><strike>假如你不给他打电话,翻到第162页。</strike></b>
——147——
尽管你知道自己不应该和他联系,但你还是决定给他打个电话。实际上,你已经接到明确的指示,不要联系他。自车祸那晚以后,你从未和他独处过,甚至连一句话也没和他说过。
他不接电话,于是你留了一则留言。你喋喋不休地谈到《惊险岔路口》,一边说一边逐渐意识到,看似深刻的想法放在电话里一说,听起来简直肤浅得难以置信。
过了几天,乔治·罗德里格斯来到你家。他是议员手下的要人。你不确定他如今的头衔是什么,但他主管筹款事宜。你和他谈过几次话,但从来没有过多交流。他很有魅力,一表人才。他长得和议员有几分相似,只是更矮些,古巴人,也更加年轻。他约摸只比你年长五岁。
他与你母亲相识,因为她在学校为议员办过一场活动。“格罗斯曼家的两位美女,”乔治说,“很高兴见到你,瑞秋。你还好吗?博卡拉顿犹太学校怎么样了?”
“我被炒了。”你母亲对他说,她的语气生硬、话里带刺,几乎像是要与他对质。
“真抱歉,”乔治说,“好吧,阿维娃,我这次来其实是为了见你。”
你们来到屋后的露台,你坐在一簇叶子花下,母亲为你们端来了冰茶。乔治等她离开,然后和善地对你说:“你不能再联系他了,阿维娃。你得往前看,这样对每个人都好。”
“这样对他好。”你说。
“这样对每个人都好。”他坚持道。
“假如我还有路可走,我自然会往前看,”你说,“我这一辈子都毁了,”你说,“没有人想雇用我。没有人想和我上床。”
“看上去也许是这样,”乔治说,“但其实没那么糟。”
“我无意冒犯,”你说,“但是你他妈怎么知道?”
乔治也答不上来。
“你懂政治,懂公关,换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
“我会回到学校。读法学,或者公共政策的硕士学位。”
“好,”你说,“暂且假设我找得到一位老师为我写推荐信,暂且假设我真的被某所学校录取,我要额外背上大约十万美元的学生贷款,然后再申请工作。那又有什么区别?你去搜索我的名字,那些东西还是在那儿,跟事发那年一样新鲜。”
乔治喝了一口冰茶。“要是你不回去读书,你可以做志愿者。重新树立自己的名声——”
“试过了,”你说,“他们也不想要我。”
“或许你需要的是证人保护制度,”他说,“新的名字,新的住所,新的工作。”
“可能吧。”你说。
“我真的不知道你该怎么办,”乔治说,“但我清楚一点……”
“什么?”
“你说没人想和你上床。这不是真的。你是个漂亮的姑娘。”
你不是个漂亮姑娘,即便是,你也知道那和性行为无关。许多丑人都有人同眠,许多相貌普通的人也有人同眠,而许多美貌的人却要孤身度过漫漫长夜。
你不是个美人。你的相貌别具风情,而你的大胸总是在向男人暗示你身姿性感、生性风流,而且头脑简单。你很清楚自己的形象,丑闻爆发后接踵而来的事情让你非常清楚旁人对你的看法。无论别人如何对你评头论足,你都不会感到惊讶了。你不可能在父母的游泳池里泡了一个夏天就突然变成了美女。话说回来,只要你肯降低标准,总是有人愿意和你上床的。你真正想说的是:我想与之上床的人都不想和我上床。
这就说明,你知道乔治这是在与你调情。
<b>假如你决定与乔治上床,翻到第151页。</b>
<b><strike>假如你请他离开,翻到第168页。</strike></b>
——151——
你走到他坐的地方,吻了他。你对他的渴望并不比其他任何人多出一分。你带他上楼,你决定和他在客房上床,而非你儿时的卧室,身边堆满高中纪念册和装裱起来的戏剧俱乐部票根。
你走进客房,锁上了门。
你感觉得到他很有经验,这样正好。虽然你身为性丑闻的主角,却对此毫无经验。
他触摸你时,你由于欢愉而浑身颤抖。你觉得自己就像一片草叶,而他是夏日里的煦风。
“如此香艳。”乔治说。
<b>翻到下一页。</b>
——152——
你错过了一次例假,但你甚至没有察觉。
<b>翻到下一页。</b>
——153——
你又错过了一次例假。
又过了几天,你发现自己正伏在马桶旁边。
“阿维娃,”母亲高声说,“你生病了吗?”
“我在矫正进食障碍。”你答道。
“这么说话太难听了。”你母亲说。
“不好意思,”你说,“我想我是真的病了。”
母亲给你端来了热汤,你用被子蒙住了头。
你看过电影,你读过小说,你有种强烈的预感,知道事态将怎样发展。
你在吃避孕药,或许是你太懒散,没有按时服药。有什么要紧的?反正也没人和你上床。
你做了妊娠测试。
蓝色的线,但是有些模糊。
你又测了一次,只是为了确保你的测试方式没有错。
蓝色的线。
你在考虑去做人流。你当然得作这样的考虑。你知道自己没有任何理由把一个孩子牵扯进你这一团糟的生活。你没有工作,没有前途,没有伴侣。你感到深深的孤独。你知道这都不足以成为让你生下孩子的理由。
你相信女性享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你绝不会为一个不支持女性选择权的人投票。
<b><strike>假如你确定做人流,翻到第155页。</strike></b>
<b>假如你决定继续怀着它,翻到第158页。</b>
——158——
大学里的最后一个学期,你选了一门高级政治学的研讨课,叫作《性别与政治》。授课人是一位年近五十的银发女子,她最近刚生了孩子。她上课时会用婴儿背囊把孩子——是个男孩——背在背上。课堂讨论时常吵得不可开交,尽管那个婴儿是研讨课上唯一的男性,他却从来不哭,相反,这些讨论让他昏昏欲睡。你不禁嫉妒那个婴儿。你希望自己也处在人生的开端,是个男性,被一位政治学家装在背囊里,背在背上。
然而那门课却平淡无奇。或许原因不在于课程,而在于你当时的情绪。丑闻渐息,而你仍然满腔忿郁。期中时,教授在课后把你留下。
“不要放弃我们这些女权主义者。”教授说。
“我没有。”你说。
“我的处境很为难。你的论文——《为什么我绝对不会成为女权主义者:对公共政策进行不分性别的研究》——这个题目或许另有含义?”她用柔和而欢快的目光看着你。
“这是斯威夫特的写作方式,”你说,“讽刺。”
“是吗?”她问。
“我为什么要做个女权主义者?出事的时候,你们没有一个人赶来支援我。”你说。
“没有,”她说,“也许我们本该站出来的。你和莱文之间的权力差距太过悬殊。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不为你辩护对公众更有益处。他是个好议员。他对女性权益也很热心。这件事无法做到完美。”
“《迈阿密先驱报》说我让女权主义运动成果倒退了50年。我有这么大的本事?”
“你没有。”
“她站在他身边。她难道没让女权主义倒退得更多?跟你出轨的丈夫一刀两断难道不是更符合女权主义的做法吗?说实话,我在这个课堂上坐了整整五个星期——更不用说我一辈子都身为女人——我还是不知道什么是女权主义者,”你说,“到底什么才是他妈的女权主义者?”
“作为一位政治学教授,在我来看,女权主义就是坚信法律面前性别平等。”
“这我当然知道,”你说,“所以我的论文到底哪里不对?”
“问题在于,性别是客观存在的,”她说,“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法律必须承认这一点,否则法律就不公平。”
“好吧,”你说,“你课后把我留下,有什么事吗?”
“你还没有进一步问我,”她说,“作为一名女性、一个人,在我看来什么才是女权主义。”
谁他妈在乎这个?你心想。
“那就是每个女性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旁人不必认同你的选择,阿维娃,但你有作出选择的权利。艾伯丝·莱文也有选择的权利。别指望旁人为你奔走呼喊。”
你竭力控制自己不翻白眼。
“我希望你能重新思考一下你的论文。”她说。
过了一个星期,你选择了退出这门研讨课。
你想留下这个孩子,即便这样做有违常理。
你没指望旁人为你奔走呼喊。
你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
时间紧迫。你还有七个月的时间改变自己的生活。
你需要一份工作,但你在网上早已臭名远扬。无论你搬到哪里都不够远。
你可以留在家里,让父母养活你和孩子。但这个孩子将是“阿维娃·格罗斯曼的女儿”,谁忍心让一个孩子从一出生就背负坏名声呢?
你可以重返校园,但那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就像你对乔治说的那样,到最后你依然是“阿维娃·格罗斯曼”。
问题在于你的名字。
<b><strike>假如你留在家里,翻到第162页。</strike></b>
<b>假如你改名,翻到第164页。</b>
——164——
网上什么都有。人们能搜到与你有关的事,但你能搜到任何事物,这样也算不失公平。你在谷歌搜索“合法改名,佛罗里达”,不到五分钟,你就查到了你需要的一切信息:办理时长,你要去什么地方,费用是多少,需要哪些文件。
你付钱作了一份背景调查,证明你没有犯罪记录。顺便说一句,你的确没有犯罪。
你到警察局去录了指纹,又签名作了公证。
你向法院提交了改名申请表。
工作人员把你的文件通读了一遍,她说:“看来都符合要求。”
“没了?”你说。
“没了。”她说。队排得很长,她并不在乎你是谁、做过什么事。她只在乎你的表格填得对不对——填得都对。你心中不禁涌起一阵对体制、对政府的感激之情。
尽管如此,你依然半是担心有人会阻止你。你担心媒体会出现。并没有人出现,或许已经没人在乎你了。你毕竟不是汤姆·克鲁斯。你不是声名远播,而是臭名远扬,也许一旦臭名远扬的人不再做臭名远扬的事情,人们就会对他们丧失兴趣。
工作人员为你安排了听证会时间。
没有人反对你的申请,于是听证会取消了。
你改了名字。
你叫简·扬。
<b>翻到下一页。</b>
你找外婆要钱。你知道她一定会给你,但这种做法依旧让你厌恶自己。
她又瘦又小,比你母亲更加瘦小。她比一个孩子大不了多少。你拥抱她的时候,感觉自己几乎要将她压碎。她穿的裤子系着细腰带,平底鞋包了跟。她的打扮一向如此。一条爱马仕围巾,一只香奈儿菱形格纹手袋。她用的东西做工上乘,选购时也花过一番心思。一旦选中,就会悉心打理。麂皮鞋子用刷子清理,项链包裹在纸巾里以免打结,手袋有专门的收纳袋,不用的时候则塞满卫生纸保持外形。你想起曾在外婆的衣帽间里度过的那些愉快的下午。“当你身无长物时,我的阿维娃,就要学会打理物件。等你生活富足时,就要做好准备,某天你可能会再次一无所有,”她常说,“打理好,就是爱。”
但凡她外出,必定会戴上耳环。今天的耳环是宝石做的——玉石、绿宝石。这是她最喜欢的一对,是她父亲为她做的,也是她从德国带来的为数不多的几件东西之一。她拥有的全部德国物品就是她带来的那些,因为她此生不肯再买德国货。她曾许诺,将在某一天把这对耳环留给你。但你非常不愿想到那个“某一天”,因为某一天她可能会死去。她离开后,还有谁会叫你“我的阿维娃”呢?
你告诉她你要离开,重新开始。你说你对于发生的一切都非常抱歉,为你给她、给梅米姨婆和整个格罗斯曼家族带来的耻辱感到抱歉。
她拿出支票簿,戴上镶有精细链条的老花镜,拿出了她专门签支票用的波点钢笔。她问你要多少。
你要了一万美金。如今的你不再像从前那样傻。你知道一万美金抵不了多长时间,但总够你重整旗鼓。
她写了一张两万美金的支票,然后把你拉到她身边。她散发着康乃馨、苹果、爽身粉和香奈儿5号的味道。“我爱你,我的阿维娃。”她说。
她的德国口音里裹挟着你名字的音节,你听见的那一刻,几乎要落下泪来。
“那个男人不是好东西,”她说,“要是你外公还在世,非阉了他不可。”
你给母亲留了一张字条,说你要离开这座城市,等你安顿好就会给她打电话。
你买了一张去缅因州波特兰市的大巴票,到达波特兰以后,你买了一辆便宜的汽车。
你开车来到了艾力森泉,父母曾经带你到这里度过假。
正值冬季,镇上空荡荡的。
你在离镇中心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公寓。只有一间卧室,不到五十平方米。为了去除前任租客留下的痕迹,墙壁被重新刷过,到处都散发着刺鼻的气味。公寓感觉大极了,因为你一无所有。
你吃着龙虾卷,思考自己能做哪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