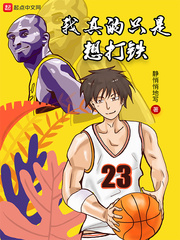奈保尔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爱米文学网aimiw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毕希西瓦先生以绝对多数获胜
“什么也不想。”他笑了,“你没注意到吗?他们对什么都无动于衷。”
侄子击败了叔叔
“他们会想到什么?”
我觉得我应该去看看穆库特先生。
“我们的人民不会首先想到国家。”
“我跟你一起去。”库戴尔先生说。当我们坐在车里时,他说:“我必须跟你一起去。多可怜,二十年了,这个人掌控着整个行政区的命运,现在却输给了自己的侄子,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侄子。”
我问他,印度的国民性是什么。
在顶楼的公寓里,前厅拉着窗帘。窗帘扯得平平的,没有一丝褶痕。穆库特先生盘腿坐在他的窄榻上,一动也不动,闭着眼睛,头扭向一边。他穿着洁白的棉布衣服,在这一刻,白色让人觉得非常触目,就像是死亡和哀痛的颜色。水磨石地板上铺着一块席子,有六个人默默地坐在那里,其中有那个戴黑色帽子的会计。库戴尔先生没有说话,走过去跟其他人一起坐在地板上。
“我们已经公布了自己的宣言,为什么还要亲自走到民众中间?拉票会变成贿选的通途。我们的人民很穷,他们不理解我们在为什么而奋斗。他们的无知被利用了。英迪拉派国大党用了几千万卢比去笼络他们,笼络农民、村民、没受过教育的人和劳工阶层,给他们口号,各种各样的口号。这就是我们的国民性。”
穆库特先生的儿子走出来,为我搬了把椅子。他俯身对父亲说:“父亲。”然后说了库戴尔先生和我的名字。起先,穆库特先生没有动。接着,他突然把头转过来,面朝着房间,神情非常痛苦,摊开一只手,用手背使劲敲打着床榻。
但对于穆库特先生其他的支持者来说,事情并不那么容易。老议员考尔先生跟穆库特先生年龄相仿,现在是印度国会上院议员。他一天只吃一顿饭,他说,这是他一九三二年坐牢时养成的习惯。而现在,他已经脱离了监狱的污秽,独立后的权力、荣耀和政治活动让他变得温和起来。考尔先生认为应该禁止个人的拉票行为。
没有人说话。
富有与贫困。但阿杰梅尔有着地域上的复杂性。拉贾斯坦是一片君主之地,但位于拉贾斯坦中央的阿杰梅尔却不是一个君主邦,那里没有大公。然而阿杰梅尔选区幅员辽阔,从阿杰梅尔到查尔集市之间的两百英里土地上,主要是沙漠、岩石和起伏的褐色山丘,开吉普都要走上六个多小时。它的两个行政区在过去属于原来的乌代浦邦,乌代浦的大公在上次选举中支持了毕希西瓦先生,但这一次,他宣布支持穆库特先生。政府“不再承认”拉贾斯坦的大公,他们的私人财源受到了威胁,于是他们各显神通,想尽办法激烈地反对政府。他们也可以把这件事情提交给人民审议,举行一次听证会,因为他们是大公。
穆库特先生的儿子把茶端了出来。他把窗帘拉开了一点,缝隙中透出装着铁丝网的窗户、照在阳台白墙上的阳光和褐色的山丘。他把一件褐色的背心披在父亲的肩上,白色触目的效果缓和了一些。
没规矩,跟老穆库特先生立场一致的人这样说,他们为那些堕落的老党员感到悲哀。Indira Hatao,反对派的海报上写着:赶走英迪拉。另一派的海报上则写着:Garibi Hatao,赶走贫困。富人,穷人:令人惊奇的是,在印度,这种基本划分用了那么久才形成了相应的政治格局。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只提供了理论。参选的各党派都发表了各自的宣言,这在阿杰梅尔的选举史上还是第一次。
“他们都在为英迪拉拉票,”穆库特先生说,“而不是那位候选人,竞选画面里根本没有他的位置。”他还没有接受自己的失败,还在诉诸人格政治的规则。我问,他和毕希西瓦先生会不会重新做朋友。他说:“我不知道。他昨天来过了,但一句话也没说。”他打开收音机,德里的六点钟英语新闻正在播报甘地夫人在全国排山倒海的胜利,播报各地老国大党人的失败,他们都和穆库特先生一样,错估了形势。
正如大家所说,英迪拉才是这次选举的核心:英迪拉,甘地夫人,新德里那位令人生畏的女人成了国会中的戴高乐,她接管了国会,废止了国会旧有的政治共识。她向特权宣战,寻求穷人、贱民和少数派的支持。她将银行国有化,不再承认大公们的身份;为了切断他们的私人财源,她还打算修改宪法。
“道德已经荡然无存,”穆库特先生说,“欧洲的马基雅维利主义<a id="noteBack_5" href="#note_5">[5]</a>政治已经污染了我们的政治,我们就要没落了。”
“我在这里工作不是为了毕希西瓦先生”,他的助选队员说,“我是为了英迪拉。”甚至到了投票当日,当他们在自己党派那五彩缤纷的帐篷里等着选民前来投票时,他们仍然在说:“这些选票不是投给毕希西瓦的,是投给英迪拉的。”
库戴尔先生站起身来。
毕希西瓦先生不怎么受欢迎。跟他叔叔比起来,他在各个方面都处于劣势。穆库特先生瘦小精干,皮肤黝黑,是苦行僧式的老派政治家,而且有过一段牢狱经历。毕希西瓦先生却身材高大,体型圆胖,像个电影明星。他是印度独立后成长起来的政客,是隶属于体制的人。跟他同属一个党派的人谈起他时会这样说:“政治是他的职业。”“如果不让他从政,他一天连两顿饱饭也吃不上。”“他叔叔为他干掉了好几百名党内工作者。”但这话不是在指责他叔叔,而是在指责毕希西瓦先生。
“身为竞选执行官,我必须在游行中露面。”我们出来后,库戴尔先生说,“否则,我的缺席会被人误解。”
牺牲:毕希西瓦先生无法高扬这样的旗帜,而且在竞选过程中,大多数时候他都显得心烦意乱,没有底气,有时候还被人穷追猛打。他不像他叔叔,穆库特先生总是谈吐自如,甚至还妙语连珠,而他却寡言少语,他的气质也让人提不起谈话的兴致。他的目光穿过镜片,茫然地盯着外面,仿佛时刻都在警惕着,生怕自己说了什么给别人落下口实。有一次,他说:“我不明白叔叔怎么能违背那些原则,那些还是他灌输给我的。”这是我从他嘴里听到的唯一一次对他叔叔的评论,他说得很快,就像是事先准备好了的。
我们在集市上赶上了游行的队伍。有人坐在卡车的车斗里,往大家身上扔彩色的小粉球。“等我七分钟,”库戴尔说着,消失在了人群中。当他心满意足地回来时,他的衣服、头发和脸上都沾着红色。红色,春天、凯旋和牺牲的颜色。
叔叔想把侄子拉下马,难道就没有错吗?“我不想让父亲参加这次竞选,”穆库特先生的儿子说,“我说,‘父亲,你现在年纪大了,而且还有残疾。’然而他的回答征服了我,让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他说,‘牺牲的时候到了。’”
一九七一年
压倒性的回答是:毕希西瓦先生错了。他应该退出竞选,不应该跟叔叔作对,叔叔对他恩重如山。穆库特先生的儿子这样说,他是穆库特先生的竞选执行官;毕希西瓦先生的竞选执行官也这样说。穆库特先生本人谈起这场竞争时,也总是流露出受伤的情绪。“当权派国大党选择了最卑鄙的武器,”他说,“让我的亲侄子来对抗我。他们知道我看重家庭感情,他们希望我能退选。”乌代浦的大公支持穆库特先生,他在一次竞选集会上说:“英迪拉派国大党正在分裂我们的国家,他们不仅在意识形态上搞分裂,还弄得我们的家庭四分五裂。”拉其普特村的村长忠于自己的大公,赞同大公的看法:“一个侄子如果不爱自己的家人,怎么可能爱公众?”
(翟鹏霄译)
穆库特先生,也就是那位叔叔,今年六十八岁,是一位双目失明的律师。他那非凡的记忆力和处理土地事务的娴熟技巧让他在拉贾斯坦享有盛名。据说,他的收费标准高达每天一千卢比,大约合五十英镑;他的年收入估计有二十万卢比,约合一万英镑。他也因为替农民无偿服务而声名远播,至今仍有农民到阿杰梅尔来寻访这位“没有眼睛的律师”。穆库特先生是老国大党员,自由战士,曾于一九四二年入狱。印度独立以来,他的政治生涯并不辉煌,但一直四平八稳,没有瑕疵:他最广为人知的政绩,也许是普及了将黄油和花生做的黄油替代品轻松地区分开来的方法。他在一九五二、一九五七和一九六二年三次为国大党赢得了阿杰梅尔的议席。一九六七年,六十四岁的他已经退休了,便把阿杰梅尔的议席交给了侄子和门生——三十六岁的毕希西瓦·巴瓦佳先生。但现在国大党分裂了,穆库特先生想要回他的席位,为了夺回它,他跟自己所有的政治宿敌结成了同盟。穆库特先生这样做对吗?毕希西瓦先生拒不交还席位,他错了吗?
<a id="note_1" href="#noteBack_1">[1]</a>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1917-1984),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尼赫鲁的女儿。担任过两届印度总理,被后人称作“印度铁娘子”。
两位重要的候选人是穆库特·巴瓦佳先生和毕希西瓦·巴瓦佳先生。穆库特先生代表的是老国大党及其所有在野同盟,他是毕希西瓦先生的叔叔,而后者正在为英迪拉<a id="noteBack_1" href="#note_1">[1]</a>派国大党争取议席。于是,阿杰梅尔人最关心的问题出现了(这也是这场关于合法性的举国之争在当地的缩影):谁在道德方面有问题?是跟侄子作对的叔叔,还是跟叔叔作对的侄子?
<a id="note_2" href="#noteBack_2">[2]</a>莫卧儿帝国实行的军事采邑性质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受封人终身享有征收封地田赋的权利。
如此说来,这次选举在某些方面就像是一家人在吵架。事有凑巧,争夺阿杰梅尔议席的两个国大党候选人恰好是亲戚。候选人共有五位,其中三位是独立候选人,不会引起太大反响。“他们参选只是出于业余爱好,”选举司的一名工作人员说,“他们会交上五百卢比的保证金,得到几千张选票,然后赔掉保证金,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仅此而已。这只是他们的业余爱好。”
<a id="note_3" href="#noteBack_3">[3]</a>湿婆的一种变身。
双方本来都想采用为老国大党赢得选举的徽标:两头套着轭的牛。但法庭已经做出裁决:决不允许使用。于是双方都为自己设计了复杂的自然主义徽标。一头母牛舔舐着吃奶的牛犊:这是以总理甘地夫人为首的国大党的徽标。一个乳房丰满的女人坐在纺车旁(丰满的乳房总是很引人注目,即便是在蜡版油印的宣传单上):这是走向对立面的老国大党(或组织派国大党)的徽标。在印度,这两个徽标的分量不相上下。纺车象征着甘地主义,母牛则意味着神圣。双方的徽标都在向世人宣告,自己这方继承了国大党正统。
<a id="note_4" href="#noteBack_4">[4]</a>印度的胡里节,又称色彩节。人们用缤纷的颜色喜迎春天,送别冬天。
投票给谁?悬挂在新德里街头的英文海报这样问道。二月中旬,我南下来到拉贾斯坦的阿杰梅尔,此时离国会选举投票日只剩两周,然而在这里,来自城市、乡村和沙漠的五十万选民似乎遇上了麻烦。国大党为印度赢得了自由,二十多年来,国大党在四次选举中连连获胜,一直是执政党。而现在国大党分裂了,分裂引发了这次中期选举。分裂的双方都在沿用国大党的名字。Kangrace ko wote do,双方的海报上都写着:投票给国大党。针锋相对的吉普宣传车上都飘扬着同样的藏红花白绿旗:吉普是竞选团最爱用的交通工具,它们驶过阿杰梅尔尘土飞扬的街道,穿梭在两轮马车、破旧的巴士、成百上千的自行车、手推车和牛车之间,营造出一种权威而紧张的气氛。
<a id="note_5" href="#noteBack_5">[5]</a>强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权术政治,认为凡有助于政治统治就都是正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