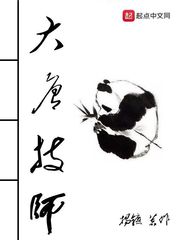第二章 (第1/5页)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爱米文学网aimiw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罗贝托和玛嘉丽塔的家坐落在圣克路丝大街,离圣玛丽娅教堂只有几个街区。教堂里的接待仪式一结束,被邀请进午餐的客人就在圣依希特罗大街的树木和阳光下鱼贯而行,向红砖、木顶的大房子走去。这所房子四周围着草坪、鲜花、栏杆,为午宴作了精心的布置。阿尔贝托大夫一到门前就看出来,欢庆活动比他本人预计的还要隆重。他出席的这地午宴,社会记者将称之为“豪华之举”。
他半窒息地离开了新婚夫妇所在的位置,在照相机的闪光灯中,一边同别人摩肩接踵一边打着招呼,好不容易地走到了花园。那里人少一些,可以喘过气来。他喝了一杯酒,挤进一群大夫中间,这些大夫都是他的朋友,拿他妻子的外出旅行没完没了地开玩笑:梅塞德斯不会回来了,一定跟了法国佬,你的额头两端开始长角了。阿尔贝托大夫一边任他们讲着,一边心里在想——他记起了体育馆的事——今天他可是出丑了。在数不尽的人头上边,他不时地看到理查德。理查德在大厅的另一端,站在说笑的男女青年中间,绷着脸,皱着眉,像喝水似的一杯杯地灌着香槟酒。“也许他是因为埃丽娅娜同安图涅斯结婚而感到难过,”大夫想,“他本来打算给妹妹找个更出众的人。”但是没有找到,大概他正在度过这种转变期的关键时刻。这时阿尔贝托大夫记起了他在理查德那个年龄也经历过这种困难阶段,在医学和航空工程学之间犹豫不决(他父亲曾用很有分量的理由来说服他,在秘鲁,航空工业工程师如果有出路,那只能是去搞风筝或航模)。也许罗贝托一头扎进生意中,不能为理查德出主意。阿尔贝托大夫鼓起勇气——这种勇气曾使他得到人们的普遍赞赏——决定在近日热情地邀请他的侄子,慎重地把事情了解清楚,巧妙地谈谈帮助他的办法。
花园里到处摆满了桌子,撑着凉伞。最深处靠近狗舍的地方支着一顶大帐篷,下边有盖着雪白台布的桌子,一字顺墙摆开,上面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冷盘。饮料间设在养了许多日本鱼的池塘旁,里边摆放了那么多杯子、瓶子,鸡尾酒会器皿、冷饮罐,好像要为一支军队解除干渴似的。身穿白上衣的年轻男侍者和头戴压发帽、腰系围裙的姑娘们,看见客人一进大门就立刻迎上前去,递上皮斯科酸酒、鸡尾酒、伏特加果汁、威士忌、杜松子酒、香槟酒以及插着牙签的奶酪、辣子土豆、腊肉樱桃、一团团的大虾、各种冷菜和利马特产的所有大开胃口的甜食。屋里,成篮的鲜花和一束束鲜花,有的靠墙放着,有的沿楼梯摆着,还有一些放在窗台和家具上,给人以清新凉爽的感觉。这些鲜花有玫瑰、晚香玉、黄菖蒲、紫罗兰、石竹花。镶木地板打了蜡,窗帘洗得干干净净,瓷器和盘碗擦得亮晶晶。阿尔贝托博士笑了,他想,连玻璃柜里的古陶瓷都擦拭一新,光泽四射。前厅里也摆了小吃,饭厅里的甜食——杏仁糖、雪糕、蛋糕、蛋青糕、蛋黄点心、椰子果、核桃粘——围着美丽的洞房花糕摆了一圈。洞房花糕是个奶油渍渍、由许多圆柱体组成的“建筑”,上面罩着薄纱,显得那么庄重,使得夫人们不时地啧啧称赞。但是,尤其引起女人好奇心的是放在二楼的礼品,看到人们排了那么长队等候观看,阿尔贝托大夫当即决定不去看,尽管他很想知道他送的手镯在礼品中居于何种地位。
当排队走近新婚夫妇时,阿尔贝托大夫高兴地听见费布列兄弟给他讲的一大串反政府的笑话。这对孪生兄弟长得如此相像,据说连他们的妻子都分辨不清。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仿佛房子马上就要倾倒,不少人原先是在花园里等着轮流进来看新郎新娘的。一群小伙子穿梭似的来来往往给宾客们送香槟酒。处处是一片笑声、开玩笑声和碰杯声,人人都说新娘漂亮极了。阿尔贝托博士终于排到了新娘跟前,他看到埃丽娅娜依然衣饰整洁,神采奕奕,尽管厅内又热又挤。“祝你永远幸福,瘦姑娘。”他拥抱着她说。新娘贴着他的耳朵说:“今天早晨小恰罗从罗马给我打来电话,向我祝贺,我和梅塞德斯伯母也说了话。她们打电话给我,真是太热情了!”红头发安图涅斯浑身大汗,脸红得像只大虾,眼里闪着幸福的火花:“现在我也应该叫您伯父啦,阿尔贝托先生?”“当然啰,侄子,”阿尔贝托大夫甩手拍了拍他,“你应该对我以你相称。”
他到处都看了一下,不断地同别人握手,接受拥抱和拥抱别人。之后,他又回到花园里,坐到一把凉伞下,慢悠悠地品尝那天的第二杯酒。一切都令人满意,玛嘉丽塔和罗贝托真会摆排场。尽管乐队的做法令他觉得不十分礼貌——撤走了地毯、小桌子和放置象牙制品的柜子,以便让舞伴们有地方跳舞——但他把这看作是对青年一代的让步而谅解这种有失高雅之举。因为众所周知,对青年来说,没有舞会的婚礼不成其为婚礼。火鸡和果酒送上来了,此刻,埃丽娅娜站在大门的第二道台阶上,正在扔花束,几十个学校的女友和邻居女伴高举双手等着接应。阿尔贝托大夫远远望见埃丽娅娜小时候的奶妈老维南希娅躲在花园的一个角落里,从心底里感到激动地用围裙边擦着眼睛。
阿尔贝托大夫步行来到欧瓦洛·古铁雷斯大街的圣玛丽娅教堂。时间尚早,客人们刚刚开始到来。他坐到前排,望着祭坛消磨时间。祭坛上装饰着百合花和白玫瑰,窗上的彩色玻璃宛如高级主教的冠冕。他又一次确认自己一点也不喜欢这座教堂,因为石膏和砖块非常不调和,椭圆形的拱门显得很浮华。大夫不时地微笑着向熟人打招呼。当然熟人不会少,大家都要到教堂来:拐弯抹角沾上边的亲戚,多年不相往来的朋友,自然,也有城里那些最显赫的人物,如银行家、大使、企业家、政治家。这个罗贝托,这个玛嘉丽塔,总是那么轻浮,大夫心里想,他对待弟弟和弟媳的弱点十分宽厚仁慈,并不刻薄。他确定午餐一定是丰盛的筵席。当奏起结婚进行曲,看见新娘走进教堂时,他的心情异常兴奋。新娘果真漂亮极了,她穿一身洁白的轻纱衣服,鹅蛋似的小脸罩着面纱,显得分外妩媚、轻柔动人;她低垂着双眼,挽着罗贝托的胳膊,向祭坛走去。罗贝托身躯肥大,表情威严,掩饰着内心的激动,露出一副主宰世界的神情。红头发安图涅斯看上去不似平常那么丑陋,身子裹在崭新的大礼服里,脸上露出幸福的光彩,就连他的母亲——一个平庸的英国女人,尽管在秘鲁已经居住了二三十年,仍旧用不好前置词——身着黑色长衣,头发卷成两层,也像是成了迷人的夫人。阿尔贝托大夫想,真是一点不错,爱情不负有心人。从小时候起,可怜的红头发安图涅斯就一直在追求埃丽娅娜,对她甜言蜜语,体贴入微,但埃丽娅娜一直傲然处之。可是,他甘愿忍受埃丽娅娜所有的粗暴言行和无礼相待,除此之外还要忍受街区的孩子们对他任意而可怕的讥讽。阿尔贝托大夫思考着:红头发是个有毅力的青年,终于达到了目的,他现在激动得面色苍白,正把戒指给利马最美丽的姑娘戴在无名指上。仪式结束了,阿尔贝托大夫在嘈杂的人群中不住地左右点头,向教堂大厅走去时,远远地望见了理查德。这个青年人好像厌恶地离开了人群,直挺挺地靠近一根柱子站着。
阿尔贝托大夫的味觉虽然没有辨出是什么品牌的果酒,但是他立刻知道了那是外国酒,可能是西班牙或智利的;不过那天他晕头转向,因而也不排除是法国的。火鸡又香又嫩,菜泥是甜奶油汁做的,还有凉拌卷心菜和葡萄干。尽管他坚持节制饮食,但还是吃了又吃。他喝第二杯果酒时,甜蜜的困意开始向他袭来,这时他看见理查德向他走来。他手中的威士忌酒杯在颤抖,双眼呆滞,闪着亮光,声音也变了:
回到家里,听说生三胞胎的妈妈想和同诊所的女友玩桥牌,做纤维瘤手术的女人曾经问过今天是否能喝罗望果酱汤,他便放心了。他答应她们玩桥牌、喝罗望果酱汤的要求。大夫慢条斯理地穿上一套深蓝色的西服、白色的丝绸衬衣,系上银灰色的领带,并且在上边别了一颗珍珠。他正往手帕上洒香水时,有人送来他妻子的来信;在信的末尾,他女儿恰罗还附上几句话。那信是从旅游的第十四个城市威尼斯寄来的,上面说:“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至少又游览了七座城市,所有的城市都美极了。”她们过得很快活,小恰罗很喜欢意大利人。“有些电影艺术家,爸爸,你想象不出他们怎样恭维我,不过,你不要告诉塔多。吻你一千次,再见。”
“伯父,还有比婚礼更愚蠢的事情吗?”理查德小声说,他对周围所有的东西都露出轻蔑的表情,随后倒在旁边的椅子上。他的领带歪到一边,一块刚刚抹上的污迹弄脏了灰色西服的衣领。他的眼睛里除了残存的酒意,还积聚着大海波涛般的愤恨。
理查德根本没有笑。他举着哑铃,满脸是汗,涨得通红,青筋突暴,满腔的怒火好像要倾泻到他们身上。大夫想,他侄子会突然把手中的哑铃扔过来,砸烂他们四个人的脑袋。他向他们告别,并且喃喃地说:“理查德,我们教堂见。”
“那么,坦白地告诉你,我对参加欢庆活动并不太热心。”阿尔贝托大夫温和地说,“但是,你可不要这样。我在你这个年龄时,还是很注意这种事的,我的侄子。”
“这个英俊的小伙子决定自杀了,大夫。”
“我从心底感到厌恶,”理查德喃喃地说,瞪着双眼,好像要把所有人都从眼底下扫除,“我不知道我他妈的到这儿来干什么。”
阿尔贝托认为,理查德做起操来会忘掉他的问题,可是他在做侧身弯时,看见理查德又露出一副怒相:显得憋闷,不耐烦,脸色十分难看。他想起他们金德罗斯家有过多位神经官能病患者。他想,在下一代的成员中,也许罗贝托的小儿子已经得了这种遗传病。然后他的思想开了小差,想到不管怎么说,来体育馆之前都应该到诊所去一下,看看那位生了三胞胎的夫人和做纤维瘤手术的女患者。他没有继续想下去,因为他需要全神贯注地做操。他一边抬腿落脚(做五十次抬腿动作!)活动躯干(三套快速扭转身体,用力呼吸!),一边遵照科克的命令,活动背部,扭转躯干,弯曲前臂,转动脖颈(用力,我的老祖宗!快点,该死的!),只有一叶肺在呼吸,只有一身皮肤在流汗,只有身上那几块肌肉在用劲,累得他也够呛了。当科克喊“拉力运动,做三次,每次十五下”时,他已经精疲力竭了。不过,出于自尊,他想至少应该用十二公斤的哑铃做上一套动作,可是已无能为力,他的力气已经耗尽了,第三次试举时,哑铃从他手上滑脱,引起了其他举重运动员的嘲讽(如果死了,就去坟墓!是鹳鸟,就到动物园去!叫殡仪馆来人!安息吧,阿门!),并且非常羡慕、默不作声地看着理查德——他一直愁眉苦脸,满脸怒气——毫不费力地完成惯常的动作。阿尔贝托大夫想,遵守纪律,持之以恒,节制饮食,有规律地生活,这还不够。这可以使差别缩小到一定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年龄就是难以克服的困难,就是高不可越的大墙了。后来,他脱光衣服走进浴室,汗水顺着睫毛流下来,迷住了他的眼睛,他伤感地反复叨念着一句在书上读到的话:“青春呀,想起你多么叫人失望呀!”他从浴室出来,看见理查德已和举重运动员聚在一起亲切地交谈着。科克对阿尔贝托大夫指着理查德,露出讥讽的表情说:
“你想想,假如你不来参加你妹妹的婚礼,她会怎么想?”阿尔贝托在思索着一些酒兴使他说出来的蠢话:难道他不曾看见理查德在喜庆活动上玩得比谁都快活吗?他的舞不是跳得很好吗?曾经有多少次,他侄子领着一群男女青年到恰罗房间里来举行即兴舞会呀?但是,他对理查德一点也没有提起这些事。他看见理查德喝干了他的威士忌,要侍者再给他斟一杯。
“做三套侧身弯,每套三十次,废物!”科克吼叫着,头上举着八十公斤,肚子鼓得像只癞蛤蟆,“收腹,不要鼓起来!”
“不管怎么说,你要准备着。”他对侄子说,“你结婚时,你父母会给你举办更盛大的庆祝活动。”
“你不要担心,伯父。”理查德对他笑笑,“红头发是个好人,既然我的瘦妹妹看上了他,一定有点缘故。”
理查德把闪闪发亮的威士忌酒杯送到嘴边,半合上眼睛,慢慢地呷了一口。随后,他头也不抬,有气无力地低声说: